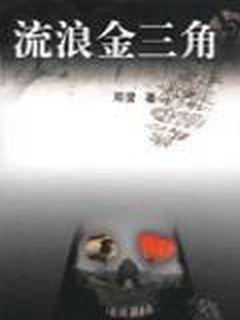- [ 免费 ] 第一章:《历史的禁区》 ...
- [ 免费 ] 第一章:历史的禁区
- [ 免费 ] 第二章:《走进金三角》 ...
- [ 免费 ] 第三章:《潘多拉魔盒》 ...
- [ 免费 ] 第四章:《铤而走险》 ...
- [ 免费 ] 第五章:《背水一战》 ...
- [ 免费 ] 第六章:土司招亲
- [ 免费 ] 第七章:封疆大吏
- [ 免费 ] 第八章:“反攻云南!” ...
- [ 免费 ] 第九章:掸邦风云
- [ 免费 ] 第十章:帝国神话
- [ 免费 ] 第十一章:“旱季风暴” ...
- [ 免费 ] 第十二章:谲波诡云
- [ 免费 ] 第十三章:大撤台
- [ 免费 ] 第十四章:《兵燹》
- [ 免费 ] 第十五章:刀锋相向
- [ 免费 ] 第十六章:危机四伏
- [ 免费 ] 第十七章:仰光枪声
- [ 免费 ] 第十八章:兵车南行
- [ 免费 ] 第十九章:“湄公河之春” ...
- [ 免费 ] 第二十章:罂粟王国
- [ 免费 ] 第二十一章:末路英雄 ...
- [ 免费 ] 第二十二章:《龙蛇争霸》 ...
- [ 免费 ] 第二十三章:坤沙出逃 ...
- [ 免费 ] 第二十四章:神秘满星叠 ...
- [ 免费 ] 第二十五章:青春似血 ...
- [ 免费 ] 第二十六章:走向深渊 ...
- [ 免费 ] 第二十七章:灵与肉
- [ 免费 ] 第二十八章:知青火并 ...
- [ 免费 ] 第二十九章:理想之光 ...
- [ 免费 ] 第三十章:朝廷招安
- [ 免费 ] 第三十一章:荡寇志
- [ 免费 ] 第三十二章:灰飞烟灭 ...
- [ 免费 ] 第三十三章:〈金三角之魂〉 ...
杏书首页 我的书架 A-AA+ 去发书评 收藏 书签 手机
繁
第二十二章:《龙蛇争霸》
2024-4-24 20:40
1
未来的掸邦革命军总参谋长张苏泉看见自己面前枪刺如林,刀刃在太阳下闪烁着青色的寒光,战队云集,钢盔像岩石,士兵方阵巍然不动。他像个真正的军队统帅,昂首挺胸,左臂紧贴裤缝,右掌像钉子一样牢牢钉在大盖帽檐之上。他记得在黄埔军校当学生时,有一次校长检阅,所有将军都踏着标准的正步,马靴在地面踏出一溜威风凛凛的烟尘。那时他想,自己有一天也要这样检阅士兵,检阅自己的部队。大地寂静,万马齐喑,惟有一人踏着将军的步伐,踏着鼓点和太阳的万道金光大步行进,走过队列,走过广场,走过群山和千军万马的受阅场面。突然军号哒哒吹响,战旗猎猎飘扬,他的一腔军人热血顿时被点燃,好像炮弹在炮膛击发,火箭点火启动,他从胸腔里迸出一句惊天动地的口号:“革—命—万—岁!”
士兵举枪响应,千山万壑呼啸:“掸—邦—万—岁!”
可惜的是,在这个几乎成为每个军人梦想的光荣时刻,在这条通往军人最高理想的伟大道路上,张苏泉不幸趔趄了一下,被一只小小的土坑,也许是泥泞水洼,或者一只突出泥土表层的挡道石块绊了一下,干扰和破坏他的行进步伐。当然他没有倒下,他只是身体短暂失去平衡。他仅仅那么歪了一下,就坚定地越过障碍,军人姿态纹丝不动,手臂还是抬得那么高,腿还是那么笔直地踢出去,继续庄严而神圣地向前行进。
当然,他面前并没有广场,没有战队云集,也没有千军万马和山呼海啸的壮观场面,这都是雄心勃勃的汉人教官张苏泉大脑中产生的幻像。这是将近四十年前张苏泉在金三角西部一个地名叫做弄亮的偏僻地方与当地自卫队见面的过程。我之所以有把握走进这位汉人军官的精神世界,是以他当时对人说过一句豪言壮语为依据:“我相信,这才是我人生的开始,我的将军之路就在脚下。”
这一天他面前只有一片泥泞的空地,空地上站立着几百名掸族士兵,这些士兵都是坤沙的队伍。他们个个衣衫不整,虽然扛枪,却不大像兵,有穿军服的,有穿便服的,还有的干脆打一条笼裾。有穿胶鞋、草鞋,更多的人打着赤脚。他们个个睁大好奇和茫然的眼睛,不是表情严肃而是近于痴呆地瞪着汉人教官,有人张开嘴巴,嘴角流出口水,他们大约觉得汉人教官的正步很古怪,很滑稽,那样走路不是很累人么?
张苏泉与其说检阅自卫队不如说检阅自己未来的人生。长长的人生之路从泥泞空地通向充满希望的未来,通向一个像太阳那样升起的金灿灿的理想世界,那就是独立的掸邦共和国。张苏泉坚信这是他事业和人生的开始。理想主义是军人的灵魂,没有灵魂的军人只有两种下场:炮灰和土匪。一面掸邦军旗猎猎引导,他的脚步更加坚定地踏向泥泞,将泥水践踏得四下飞溅。
许多年以后,当坤沙终于成为世界头号毒品大王,主宰全球百分之六十、金三角百分之八十的海洛因交易,外界依然对这个名字叫张苏泉的汉人军官一无所知。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张苏泉可以被忽略,我们熟悉许多著名政治家,如果没有他们身后站着的那些伟大的阴谋家、军事家,政治家就是一具躯壳。
2
民国三十六年(1947),成都北较场,黄埔二十期步兵科河南籍学生张苏泉以优异成绩获准毕业,怀揣一个年轻军人的勃勃雄心和辉煌的将军梦奔向战场。教官告诉学生,无论共军还是国军,都聚集着大批黄埔军校的佼佼者:陈诚、宋希濂、胡宗南、杜聿明、汤恩伯、林彪、周恩来、聂荣臻、许光达、陈赓、萧克、李达等等,这些年轻人大都在三十岁之前就当上将军,统帅大军驰骋疆场,浓墨重彩地涂写自己人生和国家历史。也许张苏泉生不逢时,他投笔从戎是为了抗战打日本,报效国家民族,但是当他毕业离开军校时,日本人已经投降,内战正起,而他由于历史的阴差阳错,注定要成为一支失败军队中的渺小一员。一个小小的见习排长,在历史大潮面前除了像一粒沙子一样随波逐流,你还能指望有什么作为呢?他没有打过一次像样的胜仗,没有一次击溃和消灭敌人,或者说他走上战场就被失败的阴影所笼罩。他所在的部队节节败退,但是命运之神还算照顾他,他没有像大多数黄埔同学那样,命丧黄泉或者进俘虏营,而是随部队退到台湾,后来又被作为战斗骨干输送到金三角反攻大陆。时易逝,功难成,几度春秋,壮怀激烈。转眼间他从一个十八岁青年变成三十多岁的中年人,而这支打了十几年仗的反共救国军却越打越没有士气,队伍垮了,地盘丢了,长官溜了,他对前途有什么信心呢?
应该感谢命运的安排,一次遭遇战使穷途末路的他与从前的部下坤沙意外重逢。人生的神秘就在于,你不知道面前的道路通向何方,或者说上帝为你安排了哪些朋友或者敌人。如果说从前打仗是为国民党卖命,那么已经三十四岁的前国民党职业军人张苏泉第一次选择了另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为异国掸邦而战。
我相信这是一种需要,就像演员需要舞台,演说家需要听众一样,军人需要功勋,需要荣誉,这一切必须源于一个伟大的奋斗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掸邦政治家坤沙先生给自己从前的军事长官重新注入了灵魂。张苏泉获得新生的标志是给自己取个掸族名字叫帕朗,以表明自己做掸邦人民儿子的决心。坤沙的武装叫弄亮自卫队,有几百条枪,他正式委任张苏泉做自卫队总教官。
坤沙为张苏泉举行了一个仪式,自卫队士兵排成方队,接受新上任的总教官检阅。张苏泉看到,这些打赤脚没有文化的掸族士兵多数连左右也分不清,值星官一声口令,大家就像陀螺一样原地乱转一气。士兵列队行进,枪上肩,甩开手臂,结果前面踢了后面的腿,后面踩了前面的脚,有人摔跤,有人掉队,乱糟糟的场面让人哭笑不得。站在一旁的坤沙看出张苏泉的心思,他平静地说:“总教官,你别以为他们都跟我一样有进取心,这些掸族人都是生性懒惰的野狗,要把他们变成军犬可得下一番功夫。”
张苏泉严肃地回答:“我的职责就是训练军队,然后带领他们打胜仗。不管什么人,只要到了我这里,我都要把他们变成合格的士兵。”
检阅之后,张苏泉说了一句话,也就是就职宣言:“士兵们,我将训练你们,把你们变成这个未来国家最优秀和最忠诚的军人。”
张坤沙在外界知名度极高,算得上臭名昭著,连贫穷的非洲人都知道他是东方的大毒枭,金三角的毒王,很少有人知道张苏泉,张苏泉是一条影子。但是在金三角,当地人则习惯将两人合称“二张”,称掸邦革命军为“张家军”,可见两人关系到了密不可分的地步。事实上1996年坤沙集团宣布缴枪,最后被缅甸政府秘密软禁在仰光的也是两个人——张坤沙与张苏泉。
张苏泉为训练张家军制定了详细计划。副总教官梁中英说,训练士兵好比生孩子,要经历十月怀胎的艰难,训练没有文化的士兵更是难上加难。跟随张苏泉的国民党军人都成了自卫队教官,他们以国民党正规军的方式训练自卫队,从立正稍息开始,站队,向右看齐,纵队,横队,分列式,齐步走,教官手握鞭子,对做不好动作或者怕苦怕累的士兵当场课以鞭打,不许吃饭,不许睡觉,罚在太阳下反复操练。
张苏泉还把国民党军队的政工制度带进自卫队。每连有政治督导员,晚上学习军人条例,汇报思想作风,由政治督导员作总结训导。纪律是军队的灵魂,张苏泉规定不许自由散漫,不许逛寨子泡姑娘,不许吸大烟喝烧酒,所有士兵必须令行禁止,违纪者轻则关禁闭,重则鞭笞直至枪毙,杀一儆百。军人就是军人,不容自行其是。整顿果然大见成效,几个月下来,平时自由散漫的掸族士兵个个如惊弓之鸟,听见口令就像听见鞭子响,军纪观念像紧箍咒一样牢牢套在他们头上。于是金三角第一次出现步伐整齐的掸族士兵队列,以及惊天动地的整齐口号。
再如敬礼,原先自卫队都是效仿政府军,行英国式军礼,腿抬得高高的,脚猛一顿,手臂高举,掌心向外翻,就像西方电影上那样极具夸张效果的动作。张苏泉甩着鞭子骂道:“奶奶的,跟劁牛卵子一样,我看见就生气!……今后都给老子改过来,像我一样,看好了——举手,敬礼!”
于是就变成中国式军礼。
由于金三角贫困原始,掸族士兵大多身材矮小体质瘦弱。张苏泉将黄埔军校的器械教学法搬进自卫队,他派人依样画葫芦地做了许多单杠、双杠、木马、平衡木和沙包,亲自给士兵作示范,强健体质。他还建起弄亮山第一座史无前例的篮球场,教会大家打篮球和进行体育锻炼。开始那些笨手笨脚的掸族人如同赶鸭子上架,许多人在单杠双杠上摔得鼻青脸肿,但是不久他们的瘦小体型就发挥出优势来,许多人变得跟猴子一样灵巧,能在器械上做出种种令人叫绝的杂技动作来。
还有射击、刺杀、进攻、隐蔽运动、匍匐前进,经过严格训练,掸族士兵掌握了许多从前一无所知的军事知识,体质明显增强,真正实现由老百姓向军人的转变。张苏泉日复一日地带领队伍出操、训练、演习,没有丝毫懈怠,他在实现自己的庄严承诺,要把这些祖祖辈辈没有走出过大山的掸族人训练成为金三角最优秀的士兵。士兵不是天生的,老百姓穿上军装依然还是老百姓,真正的士兵必须经过战争淬火。直到有一天,从瓦城回来的坤沙走近他的总教官张苏泉,他带回一个重要情报,就像演员总要登台亮相一样,他把一个崭露头角的机会摆在总教官面前。
坤沙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我看该试试牛刀了。”
3
金三角鸦片走私,自六十年代风起云涌,呈现方兴未艾之势。随着国民党军队撤台,一统天下被打破,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土司、头人、土匪、豪强势力揭竿而起,拉队伍,占山头,购武器,争地盘,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你打我,我攻你,时而结成联盟,时而互相火并,打得热热闹闹不亦乐乎。这就有些像辛亥革命的中国大地,军阀混战,群雄并起,弱肉强食,胜者为王。经过几年兼并战乱,局势渐趋明朗,金三角大小武装由数百支逐渐到几十支,其中实力最为强大,控制鸦片走私数量最多,公认群龙之首的就是果敢地区自卫队首领,西方传媒称为“鸦片将军”的罗星汉。
果敢地处金三角北端,毗邻云南临沧,居民多为汉人,是金三角为数不多的汉族聚居地,当地人称“汉人邦”。据说这些汉人的先祖都是江南人,明末为逃避清兵追杀至此,迄今已经十几代,丝毫未被当地人同化,算得上正宗汉人部落。罗星汉是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汉人领袖,民间普遍传说这个绿林强盗四条破枪起家,几起几落,后来竟打下金三角半壁江山,拥有数千装备精良的部队,控制金三角鸦片走私将近一半的数量。关于罗星汉个人经历,当地有多种说法,其中较为流行的一种是罗少年时代外出闯世界,被国民党残军招兵,入反共抗俄大学深造。五十年代末组织果敢自卫队,做起鸦片走私生意。因为果敢自卫队都是汉人,凭借这种天然的民族优势,他与国民党残军结为盟友,到六十年代国民党撤退,他的势力范围已经扩展至半个金三角地区。
我对此种说法的可靠性表示质疑,因为这种经历与另一位大毒枭坤沙过于相似,历史是一堆乱网,需要人去耐心整理。1999年春节,我的朋友王业腾邀我同往缅甸果敢做客,我因故未能成行,甚为遗憾,结果王业腾意外在果敢与早已金盆洗手的罗星汉先生不期而遇。他与罗先生交谈甚久,得知罗先生目前定居腊戌,是国会议员,为当地社会名流兼慈善家,广施钱财修公路,办福利事业,救济贫困人口,总之他的乐善好施与富甲一方同样名声在外。罗先生亲口证实,他没有当过国民党兵,但是他没有否认与国民党残军有过密切的合作。
若论叙齿,资料表明罗星汉与坤沙同龄,都生于1934年,都是汉人的后代,并且他们都与国民党残军关系很深。但是罗星汉出道早,当他声名显赫称霸金三角一方时,坤沙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人出了名,成为一方霸主,就等于成了众矢之的,把自己摆在明处,而那个同样野心勃勃的未来金三角霸主坤沙则藏在暗处,从容不迫地把罗星汉作为头号敌人,磨刀霍霍等待时机成熟。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一天,在这个没有星星和月亮的漆黑夜晚,机会终于降临了。此时坤沙坐在萨尔温江西岸、金三角边缘莱莫山区一间铁皮顶屋子里,缅甸地图标明这个地方叫当阳,距离他的对手罗星汉约有五百里路程,距离他登上世界头号毒品大王的宝座还有整整十年时间。这个未来世纪大毒枭正以一种压抑不住的兴奋声调对他的总教官说:“……罗星汉一共出动两百匹骡马,驮运十二吨鸦片,武装队伍四百人,有重武器和迫击炮。他们的目的地是大其力,但是中途可能会在景栋做成部分交易。果敢到景栋有一条大路,两条小路,骡马往返需要三个月时间……我打算不惜代价,一定要把这批货抢过来。”
据说当晚的秘密讨论持续到天亮,其间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细节,就是总教官居然当众睡着了,他垂着头,半睁眼睛,口中发出轻微的鼾声。按说这个轻慢的举动足以使坤沙感到恼火和有失尊严,大光其火,或者怀恨在心,然而坤沙不这样看。他对部下解释说这是因为总教官太辛苦的缘故,所以亲手沏了一杯酽酽的糯米红茶放在总教官面前。梁中英先生说,坤沙待人态度谦虚,从不摆架子发脾气,是个求贤若渴的领袖。我不大相信,认为有美化坤沙之嫌。我反驳说坤沙就不出尔反尔,搞阴谋诡计,两面三刀,当面是人,背后是鬼吗?
梁先生很大度,他不同我争论,他笑笑说:“也许人都很复杂吧。”
我说:“张苏泉醒来后感动吗?”
梁先生回答:“也许我们这些旁观者更感动,我们坚信坤沙是掸邦的惟一领袖。”
我认为这就是政治家的手段。如果希特勒仅仅是个疯子,几千万高傲的德意志人民何以狂热地崇拜他,跟他犯下滔天罪行?坤沙仅仅是个愚蠢的毒贩,何以那样多的职业军人死心塌地跟他跑?我悟出但凡一个人物,没有征服世界包括自己部下的个人(道德、人格等)魅力,要成就一番事业是不可想象的。
这场被称做“金三角鸦片战争”的阴谋足足策划了半个月,计划周严,滴水不漏。坤沙就像一头毒蜘蛛,在半路布下天罗地网,单等比自己大几倍的猎物撞进网里来。
4
我认为张苏泉是个真正的职业军人。职业军人的全部含义,就是一旦离开战场就等于废人。将近四十年前的那个旱季,罂粟花像天上的五彩云霞落满山坡,金三角的古老日子宁静得好像一首牧歌,然而一场血腥的战争风暴像黑云又悄悄来临。战争是军人的狂欢节,许多年后张苏泉在满星叠对美国记者说,那是他一生中打过的最大胜仗,自黄埔军校毕业起,他一直企盼这样的胜利。胜利像风,鼓起军人信心的风帆。但是后来他又改口说,他为掸邦革命而战,决非仅仅为鸦片,鸦片是革命的经费。我认为张苏泉的话道出一个事实,它表明这是国民党军人的一个历史性转变,从反攻大陆到为鸦片而战,意义非同寻常。
弄亮自卫队悄悄开出营房待命。
战争取胜的第一要素为知己知彼,也就是情报,摆在坤沙张苏泉面前的最大困难莫过于正确判断对方意图。张苏泉向国民党残军借来电台和报务员,当然不是无偿使用,而是以鸦片支付报酬。他命令副总教官梁中英亲自带领一支侦察分队,配备电台,潜入果敢地区对罗星汉马帮进行跟踪监视。
果敢位于金三角北端,距交货地点大其力路途十分遥远,从北到南横贯整个危机四伏的金三角。罗星汉马帮有三条道路可以选择;一条是景栋大路,城镇较多,关卡重重,有政府军守卫,所以罗星汉决不可能走大路,否则等于自杀。
两条小路分别是,萨尔温江西岸南班河谷的走私小道,和萨尔温江东岸老班山谷的森林小路。如果罗星汉走东路,坤沙张苏泉就只好放弃这个机会,眼睁睁看着猎物从江对岸经过而无可奈何,因为那条路不仅在水流湍急的萨尔温江以东,而且路上分别盘踞着两支势力强大的地方武装,他们是佤山的佤邦联军和割据景栋以北的东掸邦民族革命军(简称SSA)。
莱莫山位于萨尔温江西岸,坤沙只能等在西岸守株待兔。当然罗星汉决不是兔子,他当然已经料到路上肯定会有麻烦,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金三角的土匪强盗谁不垂涎他的浩浩荡荡的巨大财富呢?尽管他并不能确切地预知麻烦将出在哪里,但是以他的经验和直觉,那就是一定有人暗中打着主意。他出动了一支超乎寻常的强大武装沿途护卫就足以证明他的高度警惕。以目前已知的西岸沿途,尚无一家地方武装有足够实力和野心去抢劫这宗财富。
坤沙问张苏泉:“你说罗星汉会来吗?”
张苏泉反问:“要是你是罗星汉,你会怎么考虑?”
坤沙答:“我选择西路,否则只有从天上飞过。”
张苏泉狡黠地笑笑说:“要是你的队伍配有重机枪和迫击炮,你会不会把一支乌合之众的坤沙自卫队当成狼?反之,如果罗星汉弄到真实情报,他还会把你当成一只兔子吗?”
坤沙沉默片刻回答:“你说得对,他们走哪条路线取决于对形势的判断,我们必须给他们制造错觉。”
张苏泉说:“如果罗星汉一定要走东路,那是老天的意志。我们现在最要紧的是封锁消息,决不能走漏半点风声。胜负成败,在于情报。”
几天以后,张苏泉的预言不幸被证实,巡逻队在寨子里抓住两个罗星汉奸细。这是两个形迹可疑的掸族人,他们到处打听有关弄亮自卫队的消息,还在山上与自卫队哨兵一起喝竹筒酒,东拉西扯地厮混。奸细被巡逻队抓住的时候正在同卖米酒的掸族女人睡觉,饶舌的女人把他们当成买主,把自卫队的事情和兑了水的米酒还有自己的身体统统卖给客人。
奸细被五花大绑押到指挥部。这是两个年轻的掸族男人,毫无特别之处,把他们混同于山寨的掸族人群简直就像两滴雨水落进河中。经过仔细搜身,士兵在奸细鞋子里找到一张小纸片,上面画着一些简单的符号,根据符号的排列组合,张苏泉很快猜出这些符号所代表的意义。比如机关枪多少挺(打叉),迫击炮多少门(打勾),人数多少(画杠),驻扎位置(画圈)等等。最重要的是,他们居然弄清楚了弄亮山上来了汉人教官,还有军用电台。如果这个情报送到罗星汉手中,他能对这样一支躲在暗中虎视眈眈的军队掉以轻心吗?
坤沙往地上啐一口说:“你们知道怎么办,照老规矩办!”
梁中英老人对我解释说,正规军作战,一般不在阵地上枪毙俘虏,因为枪毙俘虏就不会再有人举手投降。但是这里不同,这里是金三角,金三角有自己的规矩。几百年来,掸族人遵循的规矩就是,俘虏可以免死,奸细必须被乱棍击毙。
我不解地说:“奸细为什么必须死?”
老人回答:“奸细是出卖,不管出卖什么人,都是可耻行为,必须受到惩罚。”
于是我眼前浮现若干年前这残酷而古老的一幕。掸族奸细明白自己难逃一死,他们多少显得有些垂头丧气,但是绝没有挣扎哀嚎或者跪地求饶的意思。他们当然也不是理直气壮大义凛然,那是革命党为主义而献身的英勇形象。他们的表情麻木,眼睛茫然而混沌地望着天空和自己的同类,像条狗,或者勒住脖子的小兽,一只鸡,一头羊,听凭同类宰杀。那是一种事不关己的顺从态度,甚至连替自己哭一哭的冲动都没有,仿佛不是自己将要被乱棍打死,变成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他们只是来代替别人出席这个仪式。据说张苏泉虽然是职业军人,以打仗为生,但是他当时还是对乱棍击毙的酷刑感到震惊。总之这两个人被一根麻绳牵着,一前一后地押出去,扛着大棒的年轻刽子手吹着口哨,轻松地跟在俘虏身后,好像屠夫跟在牲口后面一样。
张苏泉目送他们转过山坳不见了,才回过头来对坤沙说:“我想他们已经决定走西路,派出的奸细就是证明。”
5
这场后来轰动一时的鸦片大战竟然如此散漫无序,松松垮垮,前后拖了两个多月,这是所有人始料不及的。罗星汉马帮走走停停,有时干脆住下来,一住十几天,好像没有目的,也没有紧迫感,随心所欲,随遇而安,这种老百姓式的散漫旅行令阴谋家焦急万分。在沉默的煎熬中等待多日,电台终于发回情报,报告罗星汉马帮离开东岸,转上西线小路。这就是说,猎物终于要来了。
在一双双躲在暗处的眼睛严密监视下,罗星汉马帮开始加快赶路的步伐,侦察电台每天发回的情报都有新进展。这些情报在张苏泉面前渐渐勾勒出这样一幅不断延伸的行军路线图:罗星汉亲自押运鸦片渡过萨尔温江,然后与另一支马帮汇合后继续南行。由于沿途不断有马帮加入队伍,到后来马队壮大到有三百多匹骡马,押运武装也不是从前情报所说的四百人,而是变成整整八百人!这支庞大的走私武装在勐经附近离开牛车路,一头钻进无人区南班河谷,像巨蟒一样消失在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中。预计半月后他们将从西面万卡河谷中出现,这样他们就远远绕开势力强大的佤邦军和东掸邦军的活动范围,躲开敌人可能设下的埋伏。由此可见,罗星汉的行动路线是经过深思熟虑和周密思考的,现在基本可以断定,他们再次渡江的地点将会选在万卡河谷以东的圭马山附近。
侦察分队始终像影子一样尾随罗星汉后面,电波传回的情报越来越清楚地表明,这是一支武装到牙齿的走私队伍。士兵都是掸邦人称为“小汉人”的果敢华裔,他们高度警惕,随时把冲锋枪提在手中,一遇风吹草动就开枪射击。他们的战斗序列是,一队开路,一队押后,大队人马与走私货物并行。侦察员通过潜望镜看见,仅前面开路的轻机枪就有十几挺之多,火力配置相当于一支正规军。他们还发现蒙着油布的驮架下面露出驮载式重机枪的枪腿,估计至少有两门以上的迫击炮。
后来侦察员报告,一股不知死活的土匪试图夺取鸦片,被当场击毙数十人。军官下令将俘虏人头割下来,悬在树上示众。
这支戒备森严的走私大军浩浩荡荡地向南挺进,基本上无所阻挡,渐渐走近陷阱的边缘。张苏泉预设的埋伏地点是距离景栋城只有不到五十公里的孟登山。1998年我到景栋时汽车有幸从山谷中经过,我看到这里地势并不十分险要,一条小河从山脚淙淙流过,山谷里有寨子,山坡上有农人放牛,一条质量很差的沙石公路经过这里将景栋城与渡口连接起来。据说从前孟登山到处都是罂粟,后来通了公路,罂粟就转移到更远的深山里。张苏泉选择城市边缘设伏,据说当时许多部下有疑问,因为按照军事常识,这种地方不大适合打伏击,一来人多不好隐蔽,容易暴露目标,二来可能惊动城里的缅军。但是张苏泉却十分自信。他反问部下:“如果你是罗星汉,你会在什么时候放松警惕?你的队伍什么时候会前后脱节,走得松松垮垮?天气炎热,士兵为了减轻负担,都把子弹夹卸下来偷偷放在骡子背上,炮兵找不着炮架,找不着弹药。兵家云: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敌人麻痹就是最好的进攻时机。”
为了掩人耳目,张苏泉将队伍分成两队,主力趁夜晚开出莱莫山营地,神不知鬼不觉进入伏击地点隐蔽起来。另一队人马则大张旗鼓,赶了许多破牛车,声势浩大地朝相反方向的腊戌进发,好像生怕别人不知道他们要去走私一大宗货物。但是当他们走出一段路程后就扔掉破牛车,悄悄奔埋伏地点与主力会合。
当罗星汉的马队千辛万苦从万卡河谷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里钻出来,又在圭马山渡江,这样他们以为已经走过危险地段,距离景栋城也越来越近。经过长途行军,在原始森林中人困马乏,餐风宿露,护卫士兵明显放松警惕,军官也不像刚上路那样斥骂士兵,都有些听之任之的意思。侦察员报告,马队前后拖了几里路,脚夫松松垮垮,许多官兵偷偷躲在路边吸鸦片,人人都巴望赶快抵达景栋好放松歇口气。未来的金三角之王坤沙的心情又紧张又激动,他的敌人绝对没有想到,一口阴谋的陷阱已经在孟登山下掘好了。
风儿静静吹,天空艳阳照耀,马队在山道上逶迤行进,狩猎者悄悄埋伏守候。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惟有上帝的神秘之手在嘀嘀嗒嗒拨动时间。时间是万物主宰,因为谁也无法窥破未来,答案的秘密深藏于未来的帷幕之中,胜利或者失败,灾难或者幸运。
一个意外情况突然发生。
监视哨的紧急情报破坏了坤沙的好心情,驻景栋政府军约两个连,附迫击炮四门开出兵营,朝孟登山方向前来接应罗星汉马队。这个消息立刻打乱业已完成的埋伏部署,令阴谋者猝不及防。这就是说,如果政府军与罗星汉会合,坤沙自卫队不仅不占优势,而且还将陷入腹背受敌的严重困境。
6
在一片惊慌失措和悲观动摇的紧急关头,只有一个人保持了必要的清醒和镇定,他就是手握马鞭的前国民党团长和自卫队总教官张苏泉。
作为职业军人,战场的意外情况就像从天空划过的流星或者陨石,随时可能把你自以为天衣无缝的周密部署打乱,这就是人算不如天算的道理。应该说张苏泉对此早有准备,他已经派出侦察员到城里做耳目,监视政府军动向,但是他万万没有料到,一些军官公然勾结罗星汉,出动队伍前来接应他的敌人。
坤沙问张苏泉:“你看怎么办?”
张苏泉拍拍马靴,坚定地回答:“打!当然要打。放弃孟登山,换到三阳山去打。”
三阳山是座狭长的山谷,也是罗星汉马队必经之路,距孟登山有两天路程。张苏泉解释说:“如果不出意外,罗星汉应该在后天傍晚到达该地,他的前卫和后卫将把住山谷两端,马帮住进寨子宿营。我们必须赶在他们前面,也就是说,后天中午以前赶到三阳山,傍晚发起进攻。”坤沙说:“这样远的路程,我们只有一天时间,能不能赶得到?”
张苏泉回答:“学会走路就是学会打仗。胜利都是脚走出来的。”
坤沙又问:“政府军会不会尾随追击,陷我们于腹背受敌?”
张苏泉笑笑说:“那就想个办法,让他们呆在原地别动。好比爬梯子,你在下面拽他的腿,他不是就上不去了吗?”
坤沙望着老长官久经风霜的瘦脸,心里有说不出的佩服。这一年坤沙只有三十岁,严格说还是个青年,他虽然在国民党军队受过训,打过仗,但是他毕竟不是职业军人。坤沙曾在多种场合说,在真正的军人面前,没有解不开的难题,没有打不败的敌人。他所指的真正军人就是张苏泉。我由此产生一个疑问是,坤沙为什么如此信任张苏泉?这个以掸邦政治家自居的金三角头号毒枭,胸有城府,野心勃勃,他知道张苏泉能打败罗星汉,难道不能取自己而代之?张苏泉一旦羽翼丰满,他会不会威胁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设想一下,如果坤沙与张苏泉内讧,如果坤沙将大权在握的国民党教官驱逐,或者张苏泉果然野心膨胀搞起政变,金三角会有后来坤沙称霸的局面吗?坤沙会成为坤沙吗?
反过来说,张苏泉为什么要忠于坤沙?他就不能搞政变,自立山头吗?凭他的军事才能,他能带队伍打江山,难道不能自己搞走私,登上世界第一号大毒枭的宝座吗?我在金三角采访,发现张苏泉的名字似乎比坤沙更响亮,人们对他传说更多,有的简直成了神话故事,总之他是热带丛林的巴顿,金三角的常胜将军隆美尔或者朱可夫。我甚至得出一个结论:张苏泉替谁打仗,谁就将无敌于天下,成为金三角霸主。
别的毒枭,比如罗星汉,比如别的掸邦军是否收买过张苏泉?张苏泉起过异心吗?张苏泉与坤沙的伙伴关系有过危机吗?这都是谜,可惜时光流转,这些谜已经无从破译。我看到,晚年的张苏泉依然忠心耿耿追随坤沙,他们实际上已经合二为一。很显然,这已经不能用一种简单的主仆关系、利用关系或者雇佣关系来解释。我关心的问题是,究竟什么东西,政治、权力、金钱、精神、国家、民族,某种信仰还是理想主义,把两个大毒枭牢牢捆绑在一起?
张苏泉派出一支小队伍,像一群专与政府捣乱的破坏分子直奔景栋城,他们东放一阵枪,西扔几颗手榴弹,袭扰警察局,伏击巡逻车,弄得缅兵赶紧回防,全力对付城里的骚乱。自卫队主力却悄悄离开孟登山,星夜兼程赶往新的伏击地点。两天路程,只用一天一夜就提前赶到。坤沙满意地看到,他的自卫队抢先占领高地两侧,士兵不顾疲劳赶筑阵地,埋设地雷,布置火力点。张苏泉命令完成侦察任务归来的副总教官梁中英带领一支队伍插到西边山口,担任将敌人驱赶进口袋和断敌归路的重要任务。
一切就绪,张苏泉站在山坡上,他看见一轮夕阳斜斜地挂在西天,夕阳沉重而饱满,把山峦的影子都扯歪了。他从望远镜里看见一个幻像,那是一条等待已久的蛇,罗星汉马队弯弯曲曲,终于从山外的阴影游进透明的空气里。夕阳给他的敌人涂抹了一层绚烂的彩霞,那条蛇就这样披着亮闪闪的霞光慢慢向他的阵地游来。他手握着马鞭,轻轻敲打靴子,不着急,也不紧张,好像在欣赏一幅难得的美景。敌人既然进来了,当然也就出不去,这座山谷里只会有一个胜利者,那就是张苏泉。
等敌人全部进入山谷,他命令攻击。大地静了几秒钟,不是静,是时间滞留,地球停止转动。他看见一只巨大而美丽的火球从敌人后方的峡谷口升腾起来,那火球滚动着,翻腾着,变成一朵璀璨的蘑菇云,随后才有猛烈的爆炸像雷声一样隆隆地碾过宁静的空气。他知道那是梁中英向敌人后卫发起攻击,切断罗星汉的退路。四处枪炮都响起来,山谷像开了锅,爆炸的烟雾把敌人的马队团团包围起来。
罗星汉听见爆炸当然明白中了埋伏,敢于袭击他,尤其敢于在距离城市不远的地方向他袭击的人决非等闲之辈。他下令将骡马赶进寨子里,收缩队伍,等待政府军前来解围。很多年后已经成为慈善家的罗星汉先生提到那次著名的鸦片大战,他无限感慨,只说了一句话表达敬佩心情:“张苏泉是个真正的军人。”
我体会罗先生的意思,与真正的军人为敌,当然等于自取灭亡。
其实张苏泉也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他后来总结说,在金三角打仗,核心是争夺鸦片,不是杀人,即使牲口也不许射击。你把骡马打死了,多达十几吨的货物谁来运输?漫漫山道,翻山越岭,牲口是金三角惟一的运输工具,没有工具你就是打赢了也没用。这就是战争的特殊性。
夜幕降临,双方休战,山头上团团烧起篝火来。罗星汉已成瓮中之鳖,他溜不掉,或者说沉重的鸦片拖了他们后腿,人可以悄悄溜掉,鸦片和牲口却溜不掉。即将到来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山头上的张家军,战场变成浪漫之夜,兴奋和性急的掸族士兵在阵地上敲响象脚鼓,吹起笛子,跳起欢乐的火堆舞。鼓声和歌声在安静的山谷里传得很远,而那些红通通的篝火,远远看上去好像美丽发光的珍珠项链环绕在崇山峻岭的脖子上。
我猜想,此时躲在山沟里的鸦片将军罗星汉的心情可能比较痛苦,他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鸦片数量太大,没法突围,如果扔下鸦片,突围又变得毫无意义,所以他必须在这个两难选择中忍受折磨。几年后罗星汉在曼谷被捕,有记者提及这场轰动金三角的鸦片大战,罗先生从容笑答:“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
我认为罗先生是个胸怀远大的人,他决不会与鸦片共存亡,人是第一宝贵的财富,没有人,再多鸦片又有何用?这种观点比较接近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想。当然坤沙张苏泉亦然,如果罗星汉以死相拼,鱼死网破,骡马打死了,鸦片焚烧了,这样的胜利要来又有何用?所以次日黎明,攻击再次开始前,张家军向山下罗星汉下达最后通牒:“给你们两小时,要么走人,要么决战。”
罗星汉在敌人和死亡的压力下屈服了,他明智地选择了保全队伍的做法。鸦片扔了可以再来,队伍垮了就全盘皆输,所以半小时后,果敢自卫队留下骡马货物,沿来路匆匆退走了。
7
金三角最大的鸦片之战使得坤沙一举成名,他卖掉十二吨鸦片,购买武器装备,招兵买马扩充队伍。许多原国民党军人慕名前来投奔他。任何竞争归根结底都是人才的竞争,战争也不例外,所以坤沙在随后的战斗中无往不胜,扩大地盘,在金三角弱肉强食的残酷兼并中日益强大。
随着国民党帝国神话的破灭,残军势力退走,金三角出现暂时的权力真空,莱莫山头人的儿子张坤沙由于得到前国民党团长张苏泉以及一批职业军人辅佐,终于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脱颖而出,成为继国民党势力和鸦片将军罗星汉之后金三角最有势力的风云人物。他的名字开始在西方报刊上频频出现,引起东南亚国家、美国中央情报局和世界缉毒组织的注意。
未来的掸邦革命军总参谋长张苏泉看见自己面前枪刺如林,刀刃在太阳下闪烁着青色的寒光,战队云集,钢盔像岩石,士兵方阵巍然不动。他像个真正的军队统帅,昂首挺胸,左臂紧贴裤缝,右掌像钉子一样牢牢钉在大盖帽檐之上。他记得在黄埔军校当学生时,有一次校长检阅,所有将军都踏着标准的正步,马靴在地面踏出一溜威风凛凛的烟尘。那时他想,自己有一天也要这样检阅士兵,检阅自己的部队。大地寂静,万马齐喑,惟有一人踏着将军的步伐,踏着鼓点和太阳的万道金光大步行进,走过队列,走过广场,走过群山和千军万马的受阅场面。突然军号哒哒吹响,战旗猎猎飘扬,他的一腔军人热血顿时被点燃,好像炮弹在炮膛击发,火箭点火启动,他从胸腔里迸出一句惊天动地的口号:“革—命—万—岁!”
士兵举枪响应,千山万壑呼啸:“掸—邦—万—岁!”
可惜的是,在这个几乎成为每个军人梦想的光荣时刻,在这条通往军人最高理想的伟大道路上,张苏泉不幸趔趄了一下,被一只小小的土坑,也许是泥泞水洼,或者一只突出泥土表层的挡道石块绊了一下,干扰和破坏他的行进步伐。当然他没有倒下,他只是身体短暂失去平衡。他仅仅那么歪了一下,就坚定地越过障碍,军人姿态纹丝不动,手臂还是抬得那么高,腿还是那么笔直地踢出去,继续庄严而神圣地向前行进。
当然,他面前并没有广场,没有战队云集,也没有千军万马和山呼海啸的壮观场面,这都是雄心勃勃的汉人教官张苏泉大脑中产生的幻像。这是将近四十年前张苏泉在金三角西部一个地名叫做弄亮的偏僻地方与当地自卫队见面的过程。我之所以有把握走进这位汉人军官的精神世界,是以他当时对人说过一句豪言壮语为依据:“我相信,这才是我人生的开始,我的将军之路就在脚下。”
这一天他面前只有一片泥泞的空地,空地上站立着几百名掸族士兵,这些士兵都是坤沙的队伍。他们个个衣衫不整,虽然扛枪,却不大像兵,有穿军服的,有穿便服的,还有的干脆打一条笼裾。有穿胶鞋、草鞋,更多的人打着赤脚。他们个个睁大好奇和茫然的眼睛,不是表情严肃而是近于痴呆地瞪着汉人教官,有人张开嘴巴,嘴角流出口水,他们大约觉得汉人教官的正步很古怪,很滑稽,那样走路不是很累人么?
张苏泉与其说检阅自卫队不如说检阅自己未来的人生。长长的人生之路从泥泞空地通向充满希望的未来,通向一个像太阳那样升起的金灿灿的理想世界,那就是独立的掸邦共和国。张苏泉坚信这是他事业和人生的开始。理想主义是军人的灵魂,没有灵魂的军人只有两种下场:炮灰和土匪。一面掸邦军旗猎猎引导,他的脚步更加坚定地踏向泥泞,将泥水践踏得四下飞溅。
许多年以后,当坤沙终于成为世界头号毒品大王,主宰全球百分之六十、金三角百分之八十的海洛因交易,外界依然对这个名字叫张苏泉的汉人军官一无所知。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张苏泉可以被忽略,我们熟悉许多著名政治家,如果没有他们身后站着的那些伟大的阴谋家、军事家,政治家就是一具躯壳。
2
民国三十六年(1947),成都北较场,黄埔二十期步兵科河南籍学生张苏泉以优异成绩获准毕业,怀揣一个年轻军人的勃勃雄心和辉煌的将军梦奔向战场。教官告诉学生,无论共军还是国军,都聚集着大批黄埔军校的佼佼者:陈诚、宋希濂、胡宗南、杜聿明、汤恩伯、林彪、周恩来、聂荣臻、许光达、陈赓、萧克、李达等等,这些年轻人大都在三十岁之前就当上将军,统帅大军驰骋疆场,浓墨重彩地涂写自己人生和国家历史。也许张苏泉生不逢时,他投笔从戎是为了抗战打日本,报效国家民族,但是当他毕业离开军校时,日本人已经投降,内战正起,而他由于历史的阴差阳错,注定要成为一支失败军队中的渺小一员。一个小小的见习排长,在历史大潮面前除了像一粒沙子一样随波逐流,你还能指望有什么作为呢?他没有打过一次像样的胜仗,没有一次击溃和消灭敌人,或者说他走上战场就被失败的阴影所笼罩。他所在的部队节节败退,但是命运之神还算照顾他,他没有像大多数黄埔同学那样,命丧黄泉或者进俘虏营,而是随部队退到台湾,后来又被作为战斗骨干输送到金三角反攻大陆。时易逝,功难成,几度春秋,壮怀激烈。转眼间他从一个十八岁青年变成三十多岁的中年人,而这支打了十几年仗的反共救国军却越打越没有士气,队伍垮了,地盘丢了,长官溜了,他对前途有什么信心呢?
应该感谢命运的安排,一次遭遇战使穷途末路的他与从前的部下坤沙意外重逢。人生的神秘就在于,你不知道面前的道路通向何方,或者说上帝为你安排了哪些朋友或者敌人。如果说从前打仗是为国民党卖命,那么已经三十四岁的前国民党职业军人张苏泉第一次选择了另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为异国掸邦而战。
我相信这是一种需要,就像演员需要舞台,演说家需要听众一样,军人需要功勋,需要荣誉,这一切必须源于一个伟大的奋斗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掸邦政治家坤沙先生给自己从前的军事长官重新注入了灵魂。张苏泉获得新生的标志是给自己取个掸族名字叫帕朗,以表明自己做掸邦人民儿子的决心。坤沙的武装叫弄亮自卫队,有几百条枪,他正式委任张苏泉做自卫队总教官。
坤沙为张苏泉举行了一个仪式,自卫队士兵排成方队,接受新上任的总教官检阅。张苏泉看到,这些打赤脚没有文化的掸族士兵多数连左右也分不清,值星官一声口令,大家就像陀螺一样原地乱转一气。士兵列队行进,枪上肩,甩开手臂,结果前面踢了后面的腿,后面踩了前面的脚,有人摔跤,有人掉队,乱糟糟的场面让人哭笑不得。站在一旁的坤沙看出张苏泉的心思,他平静地说:“总教官,你别以为他们都跟我一样有进取心,这些掸族人都是生性懒惰的野狗,要把他们变成军犬可得下一番功夫。”
张苏泉严肃地回答:“我的职责就是训练军队,然后带领他们打胜仗。不管什么人,只要到了我这里,我都要把他们变成合格的士兵。”
检阅之后,张苏泉说了一句话,也就是就职宣言:“士兵们,我将训练你们,把你们变成这个未来国家最优秀和最忠诚的军人。”
张坤沙在外界知名度极高,算得上臭名昭著,连贫穷的非洲人都知道他是东方的大毒枭,金三角的毒王,很少有人知道张苏泉,张苏泉是一条影子。但是在金三角,当地人则习惯将两人合称“二张”,称掸邦革命军为“张家军”,可见两人关系到了密不可分的地步。事实上1996年坤沙集团宣布缴枪,最后被缅甸政府秘密软禁在仰光的也是两个人——张坤沙与张苏泉。
张苏泉为训练张家军制定了详细计划。副总教官梁中英说,训练士兵好比生孩子,要经历十月怀胎的艰难,训练没有文化的士兵更是难上加难。跟随张苏泉的国民党军人都成了自卫队教官,他们以国民党正规军的方式训练自卫队,从立正稍息开始,站队,向右看齐,纵队,横队,分列式,齐步走,教官手握鞭子,对做不好动作或者怕苦怕累的士兵当场课以鞭打,不许吃饭,不许睡觉,罚在太阳下反复操练。
张苏泉还把国民党军队的政工制度带进自卫队。每连有政治督导员,晚上学习军人条例,汇报思想作风,由政治督导员作总结训导。纪律是军队的灵魂,张苏泉规定不许自由散漫,不许逛寨子泡姑娘,不许吸大烟喝烧酒,所有士兵必须令行禁止,违纪者轻则关禁闭,重则鞭笞直至枪毙,杀一儆百。军人就是军人,不容自行其是。整顿果然大见成效,几个月下来,平时自由散漫的掸族士兵个个如惊弓之鸟,听见口令就像听见鞭子响,军纪观念像紧箍咒一样牢牢套在他们头上。于是金三角第一次出现步伐整齐的掸族士兵队列,以及惊天动地的整齐口号。
再如敬礼,原先自卫队都是效仿政府军,行英国式军礼,腿抬得高高的,脚猛一顿,手臂高举,掌心向外翻,就像西方电影上那样极具夸张效果的动作。张苏泉甩着鞭子骂道:“奶奶的,跟劁牛卵子一样,我看见就生气!……今后都给老子改过来,像我一样,看好了——举手,敬礼!”
于是就变成中国式军礼。
由于金三角贫困原始,掸族士兵大多身材矮小体质瘦弱。张苏泉将黄埔军校的器械教学法搬进自卫队,他派人依样画葫芦地做了许多单杠、双杠、木马、平衡木和沙包,亲自给士兵作示范,强健体质。他还建起弄亮山第一座史无前例的篮球场,教会大家打篮球和进行体育锻炼。开始那些笨手笨脚的掸族人如同赶鸭子上架,许多人在单杠双杠上摔得鼻青脸肿,但是不久他们的瘦小体型就发挥出优势来,许多人变得跟猴子一样灵巧,能在器械上做出种种令人叫绝的杂技动作来。
还有射击、刺杀、进攻、隐蔽运动、匍匐前进,经过严格训练,掸族士兵掌握了许多从前一无所知的军事知识,体质明显增强,真正实现由老百姓向军人的转变。张苏泉日复一日地带领队伍出操、训练、演习,没有丝毫懈怠,他在实现自己的庄严承诺,要把这些祖祖辈辈没有走出过大山的掸族人训练成为金三角最优秀的士兵。士兵不是天生的,老百姓穿上军装依然还是老百姓,真正的士兵必须经过战争淬火。直到有一天,从瓦城回来的坤沙走近他的总教官张苏泉,他带回一个重要情报,就像演员总要登台亮相一样,他把一个崭露头角的机会摆在总教官面前。
坤沙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我看该试试牛刀了。”
3
金三角鸦片走私,自六十年代风起云涌,呈现方兴未艾之势。随着国民党军队撤台,一统天下被打破,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土司、头人、土匪、豪强势力揭竿而起,拉队伍,占山头,购武器,争地盘,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你打我,我攻你,时而结成联盟,时而互相火并,打得热热闹闹不亦乐乎。这就有些像辛亥革命的中国大地,军阀混战,群雄并起,弱肉强食,胜者为王。经过几年兼并战乱,局势渐趋明朗,金三角大小武装由数百支逐渐到几十支,其中实力最为强大,控制鸦片走私数量最多,公认群龙之首的就是果敢地区自卫队首领,西方传媒称为“鸦片将军”的罗星汉。
果敢地处金三角北端,毗邻云南临沧,居民多为汉人,是金三角为数不多的汉族聚居地,当地人称“汉人邦”。据说这些汉人的先祖都是江南人,明末为逃避清兵追杀至此,迄今已经十几代,丝毫未被当地人同化,算得上正宗汉人部落。罗星汉是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汉人领袖,民间普遍传说这个绿林强盗四条破枪起家,几起几落,后来竟打下金三角半壁江山,拥有数千装备精良的部队,控制金三角鸦片走私将近一半的数量。关于罗星汉个人经历,当地有多种说法,其中较为流行的一种是罗少年时代外出闯世界,被国民党残军招兵,入反共抗俄大学深造。五十年代末组织果敢自卫队,做起鸦片走私生意。因为果敢自卫队都是汉人,凭借这种天然的民族优势,他与国民党残军结为盟友,到六十年代国民党撤退,他的势力范围已经扩展至半个金三角地区。
我对此种说法的可靠性表示质疑,因为这种经历与另一位大毒枭坤沙过于相似,历史是一堆乱网,需要人去耐心整理。1999年春节,我的朋友王业腾邀我同往缅甸果敢做客,我因故未能成行,甚为遗憾,结果王业腾意外在果敢与早已金盆洗手的罗星汉先生不期而遇。他与罗先生交谈甚久,得知罗先生目前定居腊戌,是国会议员,为当地社会名流兼慈善家,广施钱财修公路,办福利事业,救济贫困人口,总之他的乐善好施与富甲一方同样名声在外。罗先生亲口证实,他没有当过国民党兵,但是他没有否认与国民党残军有过密切的合作。
若论叙齿,资料表明罗星汉与坤沙同龄,都生于1934年,都是汉人的后代,并且他们都与国民党残军关系很深。但是罗星汉出道早,当他声名显赫称霸金三角一方时,坤沙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人出了名,成为一方霸主,就等于成了众矢之的,把自己摆在明处,而那个同样野心勃勃的未来金三角霸主坤沙则藏在暗处,从容不迫地把罗星汉作为头号敌人,磨刀霍霍等待时机成熟。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一天,在这个没有星星和月亮的漆黑夜晚,机会终于降临了。此时坤沙坐在萨尔温江西岸、金三角边缘莱莫山区一间铁皮顶屋子里,缅甸地图标明这个地方叫当阳,距离他的对手罗星汉约有五百里路程,距离他登上世界头号毒品大王的宝座还有整整十年时间。这个未来世纪大毒枭正以一种压抑不住的兴奋声调对他的总教官说:“……罗星汉一共出动两百匹骡马,驮运十二吨鸦片,武装队伍四百人,有重武器和迫击炮。他们的目的地是大其力,但是中途可能会在景栋做成部分交易。果敢到景栋有一条大路,两条小路,骡马往返需要三个月时间……我打算不惜代价,一定要把这批货抢过来。”
据说当晚的秘密讨论持续到天亮,其间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细节,就是总教官居然当众睡着了,他垂着头,半睁眼睛,口中发出轻微的鼾声。按说这个轻慢的举动足以使坤沙感到恼火和有失尊严,大光其火,或者怀恨在心,然而坤沙不这样看。他对部下解释说这是因为总教官太辛苦的缘故,所以亲手沏了一杯酽酽的糯米红茶放在总教官面前。梁中英先生说,坤沙待人态度谦虚,从不摆架子发脾气,是个求贤若渴的领袖。我不大相信,认为有美化坤沙之嫌。我反驳说坤沙就不出尔反尔,搞阴谋诡计,两面三刀,当面是人,背后是鬼吗?
梁先生很大度,他不同我争论,他笑笑说:“也许人都很复杂吧。”
我说:“张苏泉醒来后感动吗?”
梁先生回答:“也许我们这些旁观者更感动,我们坚信坤沙是掸邦的惟一领袖。”
我认为这就是政治家的手段。如果希特勒仅仅是个疯子,几千万高傲的德意志人民何以狂热地崇拜他,跟他犯下滔天罪行?坤沙仅仅是个愚蠢的毒贩,何以那样多的职业军人死心塌地跟他跑?我悟出但凡一个人物,没有征服世界包括自己部下的个人(道德、人格等)魅力,要成就一番事业是不可想象的。
这场被称做“金三角鸦片战争”的阴谋足足策划了半个月,计划周严,滴水不漏。坤沙就像一头毒蜘蛛,在半路布下天罗地网,单等比自己大几倍的猎物撞进网里来。
4
我认为张苏泉是个真正的职业军人。职业军人的全部含义,就是一旦离开战场就等于废人。将近四十年前的那个旱季,罂粟花像天上的五彩云霞落满山坡,金三角的古老日子宁静得好像一首牧歌,然而一场血腥的战争风暴像黑云又悄悄来临。战争是军人的狂欢节,许多年后张苏泉在满星叠对美国记者说,那是他一生中打过的最大胜仗,自黄埔军校毕业起,他一直企盼这样的胜利。胜利像风,鼓起军人信心的风帆。但是后来他又改口说,他为掸邦革命而战,决非仅仅为鸦片,鸦片是革命的经费。我认为张苏泉的话道出一个事实,它表明这是国民党军人的一个历史性转变,从反攻大陆到为鸦片而战,意义非同寻常。
弄亮自卫队悄悄开出营房待命。
战争取胜的第一要素为知己知彼,也就是情报,摆在坤沙张苏泉面前的最大困难莫过于正确判断对方意图。张苏泉向国民党残军借来电台和报务员,当然不是无偿使用,而是以鸦片支付报酬。他命令副总教官梁中英亲自带领一支侦察分队,配备电台,潜入果敢地区对罗星汉马帮进行跟踪监视。
果敢位于金三角北端,距交货地点大其力路途十分遥远,从北到南横贯整个危机四伏的金三角。罗星汉马帮有三条道路可以选择;一条是景栋大路,城镇较多,关卡重重,有政府军守卫,所以罗星汉决不可能走大路,否则等于自杀。
两条小路分别是,萨尔温江西岸南班河谷的走私小道,和萨尔温江东岸老班山谷的森林小路。如果罗星汉走东路,坤沙张苏泉就只好放弃这个机会,眼睁睁看着猎物从江对岸经过而无可奈何,因为那条路不仅在水流湍急的萨尔温江以东,而且路上分别盘踞着两支势力强大的地方武装,他们是佤山的佤邦联军和割据景栋以北的东掸邦民族革命军(简称SSA)。
莱莫山位于萨尔温江西岸,坤沙只能等在西岸守株待兔。当然罗星汉决不是兔子,他当然已经料到路上肯定会有麻烦,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金三角的土匪强盗谁不垂涎他的浩浩荡荡的巨大财富呢?尽管他并不能确切地预知麻烦将出在哪里,但是以他的经验和直觉,那就是一定有人暗中打着主意。他出动了一支超乎寻常的强大武装沿途护卫就足以证明他的高度警惕。以目前已知的西岸沿途,尚无一家地方武装有足够实力和野心去抢劫这宗财富。
坤沙问张苏泉:“你说罗星汉会来吗?”
张苏泉反问:“要是你是罗星汉,你会怎么考虑?”
坤沙答:“我选择西路,否则只有从天上飞过。”
张苏泉狡黠地笑笑说:“要是你的队伍配有重机枪和迫击炮,你会不会把一支乌合之众的坤沙自卫队当成狼?反之,如果罗星汉弄到真实情报,他还会把你当成一只兔子吗?”
坤沙沉默片刻回答:“你说得对,他们走哪条路线取决于对形势的判断,我们必须给他们制造错觉。”
张苏泉说:“如果罗星汉一定要走东路,那是老天的意志。我们现在最要紧的是封锁消息,决不能走漏半点风声。胜负成败,在于情报。”
几天以后,张苏泉的预言不幸被证实,巡逻队在寨子里抓住两个罗星汉奸细。这是两个形迹可疑的掸族人,他们到处打听有关弄亮自卫队的消息,还在山上与自卫队哨兵一起喝竹筒酒,东拉西扯地厮混。奸细被巡逻队抓住的时候正在同卖米酒的掸族女人睡觉,饶舌的女人把他们当成买主,把自卫队的事情和兑了水的米酒还有自己的身体统统卖给客人。
奸细被五花大绑押到指挥部。这是两个年轻的掸族男人,毫无特别之处,把他们混同于山寨的掸族人群简直就像两滴雨水落进河中。经过仔细搜身,士兵在奸细鞋子里找到一张小纸片,上面画着一些简单的符号,根据符号的排列组合,张苏泉很快猜出这些符号所代表的意义。比如机关枪多少挺(打叉),迫击炮多少门(打勾),人数多少(画杠),驻扎位置(画圈)等等。最重要的是,他们居然弄清楚了弄亮山上来了汉人教官,还有军用电台。如果这个情报送到罗星汉手中,他能对这样一支躲在暗中虎视眈眈的军队掉以轻心吗?
坤沙往地上啐一口说:“你们知道怎么办,照老规矩办!”
梁中英老人对我解释说,正规军作战,一般不在阵地上枪毙俘虏,因为枪毙俘虏就不会再有人举手投降。但是这里不同,这里是金三角,金三角有自己的规矩。几百年来,掸族人遵循的规矩就是,俘虏可以免死,奸细必须被乱棍击毙。
我不解地说:“奸细为什么必须死?”
老人回答:“奸细是出卖,不管出卖什么人,都是可耻行为,必须受到惩罚。”
于是我眼前浮现若干年前这残酷而古老的一幕。掸族奸细明白自己难逃一死,他们多少显得有些垂头丧气,但是绝没有挣扎哀嚎或者跪地求饶的意思。他们当然也不是理直气壮大义凛然,那是革命党为主义而献身的英勇形象。他们的表情麻木,眼睛茫然而混沌地望着天空和自己的同类,像条狗,或者勒住脖子的小兽,一只鸡,一头羊,听凭同类宰杀。那是一种事不关己的顺从态度,甚至连替自己哭一哭的冲动都没有,仿佛不是自己将要被乱棍打死,变成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他们只是来代替别人出席这个仪式。据说张苏泉虽然是职业军人,以打仗为生,但是他当时还是对乱棍击毙的酷刑感到震惊。总之这两个人被一根麻绳牵着,一前一后地押出去,扛着大棒的年轻刽子手吹着口哨,轻松地跟在俘虏身后,好像屠夫跟在牲口后面一样。
张苏泉目送他们转过山坳不见了,才回过头来对坤沙说:“我想他们已经决定走西路,派出的奸细就是证明。”
5
这场后来轰动一时的鸦片大战竟然如此散漫无序,松松垮垮,前后拖了两个多月,这是所有人始料不及的。罗星汉马帮走走停停,有时干脆住下来,一住十几天,好像没有目的,也没有紧迫感,随心所欲,随遇而安,这种老百姓式的散漫旅行令阴谋家焦急万分。在沉默的煎熬中等待多日,电台终于发回情报,报告罗星汉马帮离开东岸,转上西线小路。这就是说,猎物终于要来了。
在一双双躲在暗处的眼睛严密监视下,罗星汉马帮开始加快赶路的步伐,侦察电台每天发回的情报都有新进展。这些情报在张苏泉面前渐渐勾勒出这样一幅不断延伸的行军路线图:罗星汉亲自押运鸦片渡过萨尔温江,然后与另一支马帮汇合后继续南行。由于沿途不断有马帮加入队伍,到后来马队壮大到有三百多匹骡马,押运武装也不是从前情报所说的四百人,而是变成整整八百人!这支庞大的走私武装在勐经附近离开牛车路,一头钻进无人区南班河谷,像巨蟒一样消失在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中。预计半月后他们将从西面万卡河谷中出现,这样他们就远远绕开势力强大的佤邦军和东掸邦军的活动范围,躲开敌人可能设下的埋伏。由此可见,罗星汉的行动路线是经过深思熟虑和周密思考的,现在基本可以断定,他们再次渡江的地点将会选在万卡河谷以东的圭马山附近。
侦察分队始终像影子一样尾随罗星汉后面,电波传回的情报越来越清楚地表明,这是一支武装到牙齿的走私队伍。士兵都是掸邦人称为“小汉人”的果敢华裔,他们高度警惕,随时把冲锋枪提在手中,一遇风吹草动就开枪射击。他们的战斗序列是,一队开路,一队押后,大队人马与走私货物并行。侦察员通过潜望镜看见,仅前面开路的轻机枪就有十几挺之多,火力配置相当于一支正规军。他们还发现蒙着油布的驮架下面露出驮载式重机枪的枪腿,估计至少有两门以上的迫击炮。
后来侦察员报告,一股不知死活的土匪试图夺取鸦片,被当场击毙数十人。军官下令将俘虏人头割下来,悬在树上示众。
这支戒备森严的走私大军浩浩荡荡地向南挺进,基本上无所阻挡,渐渐走近陷阱的边缘。张苏泉预设的埋伏地点是距离景栋城只有不到五十公里的孟登山。1998年我到景栋时汽车有幸从山谷中经过,我看到这里地势并不十分险要,一条小河从山脚淙淙流过,山谷里有寨子,山坡上有农人放牛,一条质量很差的沙石公路经过这里将景栋城与渡口连接起来。据说从前孟登山到处都是罂粟,后来通了公路,罂粟就转移到更远的深山里。张苏泉选择城市边缘设伏,据说当时许多部下有疑问,因为按照军事常识,这种地方不大适合打伏击,一来人多不好隐蔽,容易暴露目标,二来可能惊动城里的缅军。但是张苏泉却十分自信。他反问部下:“如果你是罗星汉,你会在什么时候放松警惕?你的队伍什么时候会前后脱节,走得松松垮垮?天气炎热,士兵为了减轻负担,都把子弹夹卸下来偷偷放在骡子背上,炮兵找不着炮架,找不着弹药。兵家云: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敌人麻痹就是最好的进攻时机。”
为了掩人耳目,张苏泉将队伍分成两队,主力趁夜晚开出莱莫山营地,神不知鬼不觉进入伏击地点隐蔽起来。另一队人马则大张旗鼓,赶了许多破牛车,声势浩大地朝相反方向的腊戌进发,好像生怕别人不知道他们要去走私一大宗货物。但是当他们走出一段路程后就扔掉破牛车,悄悄奔埋伏地点与主力会合。
当罗星汉的马队千辛万苦从万卡河谷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里钻出来,又在圭马山渡江,这样他们以为已经走过危险地段,距离景栋城也越来越近。经过长途行军,在原始森林中人困马乏,餐风宿露,护卫士兵明显放松警惕,军官也不像刚上路那样斥骂士兵,都有些听之任之的意思。侦察员报告,马队前后拖了几里路,脚夫松松垮垮,许多官兵偷偷躲在路边吸鸦片,人人都巴望赶快抵达景栋好放松歇口气。未来的金三角之王坤沙的心情又紧张又激动,他的敌人绝对没有想到,一口阴谋的陷阱已经在孟登山下掘好了。
风儿静静吹,天空艳阳照耀,马队在山道上逶迤行进,狩猎者悄悄埋伏守候。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惟有上帝的神秘之手在嘀嘀嗒嗒拨动时间。时间是万物主宰,因为谁也无法窥破未来,答案的秘密深藏于未来的帷幕之中,胜利或者失败,灾难或者幸运。
一个意外情况突然发生。
监视哨的紧急情报破坏了坤沙的好心情,驻景栋政府军约两个连,附迫击炮四门开出兵营,朝孟登山方向前来接应罗星汉马队。这个消息立刻打乱业已完成的埋伏部署,令阴谋者猝不及防。这就是说,如果政府军与罗星汉会合,坤沙自卫队不仅不占优势,而且还将陷入腹背受敌的严重困境。
6
在一片惊慌失措和悲观动摇的紧急关头,只有一个人保持了必要的清醒和镇定,他就是手握马鞭的前国民党团长和自卫队总教官张苏泉。
作为职业军人,战场的意外情况就像从天空划过的流星或者陨石,随时可能把你自以为天衣无缝的周密部署打乱,这就是人算不如天算的道理。应该说张苏泉对此早有准备,他已经派出侦察员到城里做耳目,监视政府军动向,但是他万万没有料到,一些军官公然勾结罗星汉,出动队伍前来接应他的敌人。
坤沙问张苏泉:“你看怎么办?”
张苏泉拍拍马靴,坚定地回答:“打!当然要打。放弃孟登山,换到三阳山去打。”
三阳山是座狭长的山谷,也是罗星汉马队必经之路,距孟登山有两天路程。张苏泉解释说:“如果不出意外,罗星汉应该在后天傍晚到达该地,他的前卫和后卫将把住山谷两端,马帮住进寨子宿营。我们必须赶在他们前面,也就是说,后天中午以前赶到三阳山,傍晚发起进攻。”坤沙说:“这样远的路程,我们只有一天时间,能不能赶得到?”
张苏泉回答:“学会走路就是学会打仗。胜利都是脚走出来的。”
坤沙又问:“政府军会不会尾随追击,陷我们于腹背受敌?”
张苏泉笑笑说:“那就想个办法,让他们呆在原地别动。好比爬梯子,你在下面拽他的腿,他不是就上不去了吗?”
坤沙望着老长官久经风霜的瘦脸,心里有说不出的佩服。这一年坤沙只有三十岁,严格说还是个青年,他虽然在国民党军队受过训,打过仗,但是他毕竟不是职业军人。坤沙曾在多种场合说,在真正的军人面前,没有解不开的难题,没有打不败的敌人。他所指的真正军人就是张苏泉。我由此产生一个疑问是,坤沙为什么如此信任张苏泉?这个以掸邦政治家自居的金三角头号毒枭,胸有城府,野心勃勃,他知道张苏泉能打败罗星汉,难道不能取自己而代之?张苏泉一旦羽翼丰满,他会不会威胁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设想一下,如果坤沙与张苏泉内讧,如果坤沙将大权在握的国民党教官驱逐,或者张苏泉果然野心膨胀搞起政变,金三角会有后来坤沙称霸的局面吗?坤沙会成为坤沙吗?
反过来说,张苏泉为什么要忠于坤沙?他就不能搞政变,自立山头吗?凭他的军事才能,他能带队伍打江山,难道不能自己搞走私,登上世界第一号大毒枭的宝座吗?我在金三角采访,发现张苏泉的名字似乎比坤沙更响亮,人们对他传说更多,有的简直成了神话故事,总之他是热带丛林的巴顿,金三角的常胜将军隆美尔或者朱可夫。我甚至得出一个结论:张苏泉替谁打仗,谁就将无敌于天下,成为金三角霸主。
别的毒枭,比如罗星汉,比如别的掸邦军是否收买过张苏泉?张苏泉起过异心吗?张苏泉与坤沙的伙伴关系有过危机吗?这都是谜,可惜时光流转,这些谜已经无从破译。我看到,晚年的张苏泉依然忠心耿耿追随坤沙,他们实际上已经合二为一。很显然,这已经不能用一种简单的主仆关系、利用关系或者雇佣关系来解释。我关心的问题是,究竟什么东西,政治、权力、金钱、精神、国家、民族,某种信仰还是理想主义,把两个大毒枭牢牢捆绑在一起?
张苏泉派出一支小队伍,像一群专与政府捣乱的破坏分子直奔景栋城,他们东放一阵枪,西扔几颗手榴弹,袭扰警察局,伏击巡逻车,弄得缅兵赶紧回防,全力对付城里的骚乱。自卫队主力却悄悄离开孟登山,星夜兼程赶往新的伏击地点。两天路程,只用一天一夜就提前赶到。坤沙满意地看到,他的自卫队抢先占领高地两侧,士兵不顾疲劳赶筑阵地,埋设地雷,布置火力点。张苏泉命令完成侦察任务归来的副总教官梁中英带领一支队伍插到西边山口,担任将敌人驱赶进口袋和断敌归路的重要任务。
一切就绪,张苏泉站在山坡上,他看见一轮夕阳斜斜地挂在西天,夕阳沉重而饱满,把山峦的影子都扯歪了。他从望远镜里看见一个幻像,那是一条等待已久的蛇,罗星汉马队弯弯曲曲,终于从山外的阴影游进透明的空气里。夕阳给他的敌人涂抹了一层绚烂的彩霞,那条蛇就这样披着亮闪闪的霞光慢慢向他的阵地游来。他手握着马鞭,轻轻敲打靴子,不着急,也不紧张,好像在欣赏一幅难得的美景。敌人既然进来了,当然也就出不去,这座山谷里只会有一个胜利者,那就是张苏泉。
等敌人全部进入山谷,他命令攻击。大地静了几秒钟,不是静,是时间滞留,地球停止转动。他看见一只巨大而美丽的火球从敌人后方的峡谷口升腾起来,那火球滚动着,翻腾着,变成一朵璀璨的蘑菇云,随后才有猛烈的爆炸像雷声一样隆隆地碾过宁静的空气。他知道那是梁中英向敌人后卫发起攻击,切断罗星汉的退路。四处枪炮都响起来,山谷像开了锅,爆炸的烟雾把敌人的马队团团包围起来。
罗星汉听见爆炸当然明白中了埋伏,敢于袭击他,尤其敢于在距离城市不远的地方向他袭击的人决非等闲之辈。他下令将骡马赶进寨子里,收缩队伍,等待政府军前来解围。很多年后已经成为慈善家的罗星汉先生提到那次著名的鸦片大战,他无限感慨,只说了一句话表达敬佩心情:“张苏泉是个真正的军人。”
我体会罗先生的意思,与真正的军人为敌,当然等于自取灭亡。
其实张苏泉也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他后来总结说,在金三角打仗,核心是争夺鸦片,不是杀人,即使牲口也不许射击。你把骡马打死了,多达十几吨的货物谁来运输?漫漫山道,翻山越岭,牲口是金三角惟一的运输工具,没有工具你就是打赢了也没用。这就是战争的特殊性。
夜幕降临,双方休战,山头上团团烧起篝火来。罗星汉已成瓮中之鳖,他溜不掉,或者说沉重的鸦片拖了他们后腿,人可以悄悄溜掉,鸦片和牲口却溜不掉。即将到来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山头上的张家军,战场变成浪漫之夜,兴奋和性急的掸族士兵在阵地上敲响象脚鼓,吹起笛子,跳起欢乐的火堆舞。鼓声和歌声在安静的山谷里传得很远,而那些红通通的篝火,远远看上去好像美丽发光的珍珠项链环绕在崇山峻岭的脖子上。
我猜想,此时躲在山沟里的鸦片将军罗星汉的心情可能比较痛苦,他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鸦片数量太大,没法突围,如果扔下鸦片,突围又变得毫无意义,所以他必须在这个两难选择中忍受折磨。几年后罗星汉在曼谷被捕,有记者提及这场轰动金三角的鸦片大战,罗先生从容笑答:“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
我认为罗先生是个胸怀远大的人,他决不会与鸦片共存亡,人是第一宝贵的财富,没有人,再多鸦片又有何用?这种观点比较接近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想。当然坤沙张苏泉亦然,如果罗星汉以死相拼,鱼死网破,骡马打死了,鸦片焚烧了,这样的胜利要来又有何用?所以次日黎明,攻击再次开始前,张家军向山下罗星汉下达最后通牒:“给你们两小时,要么走人,要么决战。”
罗星汉在敌人和死亡的压力下屈服了,他明智地选择了保全队伍的做法。鸦片扔了可以再来,队伍垮了就全盘皆输,所以半小时后,果敢自卫队留下骡马货物,沿来路匆匆退走了。
7
金三角最大的鸦片之战使得坤沙一举成名,他卖掉十二吨鸦片,购买武器装备,招兵买马扩充队伍。许多原国民党军人慕名前来投奔他。任何竞争归根结底都是人才的竞争,战争也不例外,所以坤沙在随后的战斗中无往不胜,扩大地盘,在金三角弱肉强食的残酷兼并中日益强大。
随着国民党帝国神话的破灭,残军势力退走,金三角出现暂时的权力真空,莱莫山头人的儿子张坤沙由于得到前国民党团长张苏泉以及一批职业军人辅佐,终于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脱颖而出,成为继国民党势力和鸦片将军罗星汉之后金三角最有势力的风云人物。他的名字开始在西方报刊上频频出现,引起东南亚国家、美国中央情报局和世界缉毒组织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