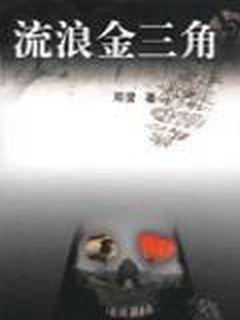- [ 免费 ] 第一章:《历史的禁区》 ...
- [ 免费 ] 第一章:历史的禁区
- [ 免费 ] 第二章:《走进金三角》 ...
- [ 免费 ] 第三章:《潘多拉魔盒》 ...
- [ 免费 ] 第四章:《铤而走险》 ...
- [ 免费 ] 第五章:《背水一战》 ...
- [ 免费 ] 第六章:土司招亲
- [ 免费 ] 第七章:封疆大吏
- [ 免费 ] 第八章:“反攻云南!” ...
- [ 免费 ] 第九章:掸邦风云
- [ 免费 ] 第十章:帝国神话
- [ 免费 ] 第十一章:“旱季风暴” ...
- [ 免费 ] 第十二章:谲波诡云
- [ 免费 ] 第十三章:大撤台
- [ 免费 ] 第十四章:《兵燹》
- [ 免费 ] 第十五章:刀锋相向
- [ 免费 ] 第十六章:危机四伏
- [ 免费 ] 第十七章:仰光枪声
- [ 免费 ] 第十八章:兵车南行
- [ 免费 ] 第十九章:“湄公河之春” ...
- [ 免费 ] 第二十章:罂粟王国
- [ 免费 ] 第二十一章:末路英雄 ...
- [ 免费 ] 第二十二章:《龙蛇争霸》 ...
- [ 免费 ] 第二十三章:坤沙出逃 ...
- [ 免费 ] 第二十四章:神秘满星叠 ...
- [ 免费 ] 第二十五章:青春似血 ...
- [ 免费 ] 第二十六章:走向深渊 ...
- [ 免费 ] 第二十七章:灵与肉
- [ 免费 ] 第二十八章:知青火并 ...
- [ 免费 ] 第二十九章:理想之光 ...
- [ 免费 ] 第三十章:朝廷招安
- [ 免费 ] 第三十一章:荡寇志
- [ 免费 ] 第三十二章:灰飞烟灭 ...
- [ 免费 ] 第三十三章:〈金三角之魂〉 ...
杏书首页 我的书架 A-AA+ 去发书评 收藏 书签 手机
繁
第九章:掸邦风云
2024-4-24 20:40
1
自从在孟萨吸毒之后,钱大宇在我心目中变得越发神秘莫测。他究竟是什么人?从事什么职业?有什么背景?是贩毒集团,还是台湾派来的特务,或者是什么秘密组织成员?他为什么关心我的采访,仅仅因为同他父亲钱运周有关?
我想,我在对方心目中是怎么回事呢?作家,采访?还是另有企图?我想他大约也觉得邓贤是个身份神秘的家伙,因为我们都没法窥破对方的秘密。离开孟萨前,我提出上拉牛山口看看,听说那里还有部分战场遗迹,而李弥时代最大规模的战争就发生在那里。
我们的汽车开出一段砂石路面,很快就上了山。最初路面尚可,汽车开得较快,道路两旁的掸族山寨一晃而过。这条公路是通往山外的惟一公路,但是很少看见对面有车过来,冷清清的路面让人感到寂寞,偶尔见掸族人赶着牛车慢吞吞地走路。随着山势越来越陡险,路面变得越发糟糕,经雨季浸泡而变得又滑又软的红泥好像牛皮糖一样包裹着车轮,汽车不仅在坑坑洼洼的路面上跳舞,而且像个脚步不稳的老人趔趔趄趄直打滑,我的心提到喉咙眼上了。
忽然间就出事了。
我还来不及反应过来,汽车轰的一震,我们的头一齐重重撞向车顶,原来汽车滑进路边水沟里。幸好是公路内侧,我们爬出车来向外面看看,个个都变了脸色。公路外侧是座云遮雾绕的深谷,能听见溪水在谷底吼叫,上帝保佑,要是他老人家让汽车滑向另一个方向,我们只好永远从这个险恶的世界上消失了。
好容易把车弄出水沟,司机小董说什么也不肯往前开,车是他一家人的谋生的饭碗,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这个蚀本生意就做大了。我认为安全第一,但是效率也很重要,如果司机有把握开下去,乘车总比走路好。钱大宇的态度很奇怪,他既反对开车,也反对走路,他说:“要是走路,今天夜里也走不到,要是开车,下次一定往外面打滑,不然我们来打个赌。”
我说:“你要怎么样?调架直升飞机来?”
他望望山头,很有把握地说:“前面有个寨子,司机你把车开下山等着,我们骑马上山。”
汽车留在公路上,我只好跟着他,步行大约二三十分钟,就看见芭蕉树丛中露出几幢铁皮屋顶。在金三角,人们盖房子一律采用铁皮顶,既不用砖瓦,也不用茅草,你看见哪里有铁皮顶在太阳下反光,哪里就有人家和山寨。面前是座汉人寨,说得好听是华侨,其实就是当地山民,在我看来同掸族山民也没有什么区别。他们说的都是掸族话,钱大宇同他们叽叽咕咕说一阵,我一点也听不懂。一个男人同意为我们当向导,说好我付路费,两百泰铢,约合人民币五十元,我认为这个价钱不错,他牵来两匹矮种马,跟中国内地毛驴差不多,我们一人骑一匹就上路了。
这是我有生以来头次取得骑马的经验。矮种马的胯骨一动一动,肚子也一鼓一缩地呼吸,仿佛提醒我胯下是个活物。我感到很别扭,这个活物无论上坡下坡,随时让我神经紧张,我觉得自己这么沉重的身体压在这头可怜的牲口身上,而且坐不稳当,老是滑来滑去,弄出一头汗来,好像跟谁搏斗一样。我相信自己的表情看上去一定可笑极了。山民姓秦,皮肤黢黑,属于那种不好辨认年纪的人,我认为他的年龄应该在二十岁到五十岁之间。他看出我很紧张,就用汉话安慰我说:“不要紧,这匹马能驮二百斤呢。”我说:“是吗?驮这么重,一天能走多少里?”老秦说:“八九十里地吧。”我听出老秦有云南口音,就问他是哪儿人?他茫然地摇摇头,好像没有听懂。我说:“我知道你是汉人,老家在云南什么地方?”钱大宇在后面接口回答:“他们在金三角几代人,哪里弄得清云南老家在什么地方?”
山上雾大起来,如果从山下看,这不是雾,是云,山道上到处湿漉漉的。马儿驮着沉重的我倒没有什么抱怨,它很听话,任劳任怨,头有规律地一点一点,好像在背诵英语单词。我渐渐习惯同它和谐相处,不再紧张。树林越来越高大茂密,空气中有种浓浓的腐叶生霉和动物的腥骚气味,四处寂静无声,只有树叶上不时滚落很响的水滴声,好像下雨一样。这是一处真正的热带雨林,我看见连空气也是绿油油的,玲珑剔透,我深深吸了一口气,浑身舒畅,有种醉氧感觉。我想森林多好啊,也许会有老虎、猴子,还有野象,但是最好不要有人。在这个世界上,人是罪恶之源,只要有人就会有污染,有犯罪,人类像丑陋的苍蝇,把文明的罪恶播向四面八方。
正想着,好像上帝有意验证我的预感,密林深处忽然冒出一队驮载货物的沉甸甸的马帮,与我们迎面相遇。空气中立刻多了一种浑浊刺鼻的人与动物的混合气味。我看见马背上耸立着结实的驮架,驮架吱吱呀呀响着,上面盖着油布,马蹄沉重地将泥水踏得飞溅起来。马儿喷着粗粗的热气,不时打着响鼻,看得出走了很长的山路。赶马人个个面色黢黑,戴尖竹笠披棕蓑衣,沉默地从我们身边擦肩而过。他们仿佛一心一意赶路,对狭路相逢的我们不感兴趣。我们赶紧让在一边,闻着空气中人马散发的浓烈汗臭,等待他们先过,这是山里的规矩,相当于交通规则的空车让重车。忽然有件什么硬邦邦的东西撞我一下,我被电击一般,险些叫出声来。原来这个赶马人的蓑衣下面,露出一截黑黝黝的枪管来。
天!走私毒品……匪帮!
2
我要说明的是,我决不是个勇敢的人,在我偶然发现这支武装马帮之后,我的心跳立刻发生紊乱,大脑缺氧,浑身发冷一样打哆嗦。我想我当时血压一定高得惊人。与贩毒集团迎面相遇,就跟与老虎迎面相遇一样,你能事先作出什么正确反应呢?我脑子一片空白,就像发生故障的电视屏幕。好容易等到这队人马走过去,什么事情也没有出,那些带枪的人对我们视而不见,我松了一口气,胆子立刻大起来。我掏出照相机,躲在树后想偷拍几张照片,这将是珍贵的现场抓拍,没准还能得大奖。这个想法令我激动得发抖。
突然一只大手从后面把我按倒在地上。
原来是钱大宇。他怒不可遏,恶狠狠地咬着我的耳朵嚷道:“你他妈的不要命了?你活够了,我可没打算跟你一起送命!”
等我从地上爬起来,马帮已经不见影子,相机镜头沾满泥水。我气得发抖,嘴唇哆嗦说不出话来,要不是这家伙横加阻拦,我相信照片已经偷拍成功,要知道我是多么需要照片,需要成功,将来我的书出版,这些宝贵照片表明我是冒着多大危险闯进金三角,拍摄下来关于丛林中贩毒集团的真实镜头。现在一切都毁了,毁在一个对写作和文学一窍不通的混蛋手中。
钱大宇看看相机,再看看愤怒的我,他没有说话,拾起相机扔给我,转身上马继续往山上行进。我无可奈何,只好怏怏地跟在后面。说实在话,此刻我无法怨恨或者跟他赌气,离开他我能上哪里去呢?
走了一程,钱大宇说话了。他说:“老兄,相机弄脏了,我很抱歉,回去我替你擦一擦。”
我懒得开腔,不想答理他。他知道我还在生气,就说:“你不懂金三角规矩,看见别人的事,把眼睛和嘴巴一齐闭上。不然你就大祸临头了。”
我问:“他们是什么人?毒品走私集团?”
钱大宇说:“也许只是一般走私,也许挟带毒品,谁说得清呢?”
我叫起来:“他们有枪啊!”
钱大宇回答:“这有什么稀奇?你问问老秦,他们寨子里谁没有枪?”
原来如此!我们又走了很久的路,终于在中午时分登上拉牛山口,这时老天好像欢迎我们到来,云开雾散,天空突然放晴了。我看见这真是一架气势雄伟的大山,山垭口像一扇小门,扼住孟萨坝子出口。极目远眺,蜿蜒的萨尔温江像一条跳跃的金腰带,环绕群山之间,在正午的阳光下闪闪发光。钱大宇指着脚下山头介绍说:“决战就在这里展开,我父亲受了伤,印度雇佣军司令自杀,李弥下令树碑纪念呢。”
向导老秦熟悉地形,带领我们拨开荒草,来到一座石壁下。我赫然看见一块石碑,高约两三米,阔一米许,其实也不是石碑,而是刻在石头上的一排文字。年代久远,石头慢慢风化剥落,那些字迹有的看得清,有的已不可辨认,我认出并抄录内容如下:
中国救国军亡永垂总指挥李弥中华民十一年亲立
我想起八十年代在滇西松山战场上也有一块同样的石碑,为李弥亲立,也是纪念同一支队伍阵亡将士忠魂,不同的那是抗日战场,军人为祖国而战,为驱逐侵略者而献身,而这里是缅甸,是金三角,他们算什么呢?侵略者?烈士?毒贩?非法武装?他们应该名垂青史,还是遗臭万年?
老秦动作麻利地拔去四周荒草,恭恭敬敬跪下来磕了三个头。他的神情极为虔诚,口中念念有词,是当地话,我听不懂。我悄悄问钱大宇:“他是残军后代?”
钱大宇语气淡淡地说:“他爷爷和大伯都死在战场上。”
我觉得一股寒气从脚下渗出来。我说:“拉牛山决战你们死了多少人?”
这个“你们”很生硬,不像同胞,很没有同情心。钱大宇看我一眼答:“好像有五六千吧,但是消灭敌人一万多。”
我自豪不起来,这个数字令我震惊,相当于集体屠杀!我想象不出,数以万计的军人尸体铺满山野是怎样一种壮烈场面!但是五十年岁月过去,战争硝烟散尽,弹指一挥间,拉牛山依然山明水秀,郁郁苍苍,但是那些生命却化作泥土,化作轻烟,消失得无影无踪。
…………
下山已是夕阳西斜,我看见一头真正的野兽,那是一头美丽的褐色山鹿,披着金灿灿的晚霞从容不迫走过山坡,走过绿油油的大自然,然后从我们视线中消失。我呆呆地看着这个自由的美丽生命走远,心中一时充满感叹和惆怅。如果金三角没有枪声,没有毒品,它本该是万物的乐园啊!
这天的惟一的遗憾是相机进了水,没能拍成照片。
3
我继续关注国民党帝国在金三角的崛起。
封疆大吏李弥踌躇满志,该做的姿态都做了,反攻云南也反攻了,朝思暮想的美国武器搞到手,应该说最大赢家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更不是美国人,而是他李弥。一切皆在运筹帷幄之中。搞政治就是这么回事,反攻是态度,打仗是实力,谁能阻止他打败仗呢?就像谁也无法制止天要下雨一样。他正是因为“反攻失利”而博得头彩,中了一个大奖。台湾卵子大的地方,达官显贵多如牛毛,而在这片面积比台湾大几倍的金三角,他李长官的头昂得比谁都高,谁敢与他比肩?他是金三角的主宰,金三角的太阳,一切惟他意志是从。权力,多好啊,就像日月和风一样无所不在,有权力就有一切。
军权是权中之权。李弥回孟萨第一件事就是进行军队大整编。整编后的反共救国军摇身一变,俨然具备小国防部的格局:一个总部,下辖司政后三部,一个北方作战指挥部,四大军区,三大主力师,十八支挺进纵队和四个边区独立支队。他亲自任命高级军官,其中包括副总指挥多名,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军区司令以及军、师长均为他从香港带来的亲信。原复兴部队只除一个李国辉继续留任师长外,其余皆名落孙山。而担任第一副总指挥的不是别人,正是刚刚偕同李太太从昆明狼狈出逃的前第八军副军长柳元麟。
空运来的武器被严密存放在孟萨大本营中,这批武器足够装备三个国际标准师,但是李弥并不打算把它们全部补充到部队去。他只将其中部分配备主力师,其余各纵队支队杂牌军游击队,武器装备自行筹措。他的做法与从前蒋介石如出一辙:亲疏有致,内外有别,中央军是嫡系,地方部队杂牌军是野种,听任自生自灭。
从前李国辉时代,复兴部队对掸邦土司采取安抚政策,经常送礼物武器笼络他们。但是李弥不同。李弥是堂堂国民党陆军中将,反共救国军总指挥兼云南省主席,如果按清朝官位,少说也得封个从一品文武大员。那些土司算什么呢?充其量是些不开化的蛮子、部落酋长,他们有什么资格与李长官平起平坐,被他待若上宾呢?如果说从前李国辉力量薄弱有求于土司,“借土养命”,那么以现在反共救国军的强大实力,谁还敢与他公开作对,在老虎头上捋毛呢?
五十年代岁末的一天,李弥派出信使向金三角各大土司送去请帖,通知土司三天之内到孟萨开会,请帖对会议内容含糊其辞地称:“协调有关方面……管辖职能范围以及鸦片粮食税收等重大问题,恭请出席为要。”云云。
钱大宇的外公孟萨土司刀栋西是最早接到开会通知的人。
世袭大土司对汉人这种集中议事方式感到很不理解,因为在金三角,土司老爷从来不开会,如果有什么要事相商,大家就像走亲戚一样,你来我往,马队浩浩荡荡,今天你到我官寨来,明天我到你府上去,所以大家从来没有聚在一起的机会。据说从前土司父亲的父亲也就是老土司曾经接到一次类似的开会通知,那次是仰光英国总督专程派信使送来的,结果老土司的马队在路上走了三个月,到仰光后却只开了一天会。
开会内容同样让刀土司感到迷惑不解。“重新协调……管辖职能范围”是什么意思?土司的领地是从老土司手中传下来的,老土司是从更老的土司手中传下来的,就像坝子里的水是从山里流下来,大树再高也得从树根开始生长一样,难道那些汉人不明白,水是不能流回山上去的,树是不能从树梢开始生长的么?还有“鸦片、粮食、税收”是什么意思,莫非那些从中国来的汉人要土司向他们交纳鸦片、粮食和税收不成?
不仅刀土司不明白,连足智多谋的汉人管家也弄不明白,这是一个从来没有人遇到过的难题,连官寨里胡子最白的老人也没有遇到过,所以人们都被难住了。土司只好悄悄派人把当军官的汉人女婿钱运周叫回官寨,好把事情弄个明白。
钱运周也不清楚会议内情,但是他能猜到李长官要统一金三角的决心,没有人能够阻挡李长官的意志。所以他委婉开导土司岳父“识时务者为俊杰”的道理,指出开会无论李主席号召什么他都要无条件服从,带头拥护响应。
尽管这个道理属于汉人而不是掸族,刀土司对这种“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的汉人逻辑很抵触,但是他懂得要服从强权意志这个大原则,这个原则在地球上是一致的,好比动物天生知道弱肉强食的道理,所以土司老爷勉强接受了女婿的建议。后来他果然处处按照女婿的指点去做,获得意想不到的好处。
4
我能想象这是一个充满杀机和危机的会议,当身着国民党将官制服的李主席满脸微笑,亲自同与会土司握手,土司个个矮了半截,唯唯诺诺。副官长宣读以李主席名义发布的三项政策:第一,所有金三角地区,北至佤邦果敢,南到孟卯耶县,均为反共救国军管辖区。第二,凡军管区内居民,均要征收赋税和公粮,征收数目由军方决定。土司、山官和头人享有免交特权。第三,对鸦片实行统购政策,由军方统一制订收购价,任何人不得私自买卖鸦片。商人须经批准方可进入军管区做生意。最后这位汉人军官杀气腾腾地补充道:“凡遵守政策条令者,其领地将受到军队保护,违者严惩不贷。”
众土司面面相觑,敢怒不敢言。
几百年来,萨尔温江以东这片辽阔的崇山峻岭都是土司老爷们的领地,山高皇帝远,连仰光的英国人都管不到这里来,一切由土司说了算。金三角是土司的家,土司是金三角的老爷。奴才向老爷交税纳贡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商人当然也要纳贡,那是向土司纳贡,纳什么贡和纳多少贡视土司心情兴致而定。可是眼下这位在中国云南打了败仗的汉人主席却要像主人一样命令商人和老百姓向他交税纳贡,还要抢走土司世世代代赖以为生的鸦片生意。你是汉人主席,要收税回你们云南收好了,怎么收到金三角来了呢?
土司们脸色都很难看,会议陷入僵局。问题是他们没有胆量反抗,因为他们的眼睛决不会看不到在会场外面游动的武装士兵,还有那些虎视眈眈的机枪大炮。这就是强权政治。李弥是政治家,他当然知道怎样对付这群没有见过世面的土司老爷,他没有强迫大家表态,而是摆下丰盛的酒席请土司们喝酒。
李主席亲自向土司敬酒,这杯酒当然是苦酒,喝得比较勉强,但是没有人敢不喝下去。钱大宇的外公刀土司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下子完成认识过程的飞跃。当尊贵的汉人主席同他干杯时,尽管他心里并不高兴,也有许多抵触和思想疙瘩,但是他牢记女婿的话,坚决服从汉人长官领导。掸邦有句谚语:猴子不该与老虎争食。如果老虎不幸闯进猴子家里,那并不是老虎的错,猴子只好自认倒霉。作为猴子之一的刀土司果然旗帜鲜明地宣布站在汉人一边。
“我,刀土司……欢迎李主席住在孟萨,这是我刀土司的光荣。”可怜的土司老爷一看到汉人主席亲切和鼓励的目光,立刻乱了方寸,话也说得词不达意:“今后,我们掸邦人,把粮食统统交给李主席,买卖也做在一起,饭也吃在一起,就像亲兄弟一样……你们都知道,我的女婿,也是李主席的军官,我们都是亲戚。”
这番逻辑思维混乱的表态至少传达出一个令人满意的思想,那就是坚决拥护汉人军队的领导。这当然有些像带头在条约上签字的卖国贼,出卖的不仅是自己,还有其他土司的共同利益。许多人坐不住了,纷纷表态服从李主席,当李弥得知原来大土司的女婿就是师参谋长钱运周时,便大大地赞扬了孟萨土司,并号召所有土司向他学习。当然也有少数坚持不识时务的人,孟畔土司自恃与东枝掸邦首领有亲戚关系,带领另外一群小土司和头人提前退出会场。李弥脸上也不见生气,他对大家讲了一个驴子欺骗老虎的笑话,说的是驴子自作聪明,结果被老虎作了午餐。听得土司毛骨悚然。
当客人酒足饭饱醉眼朦胧的时候,一场事先安排的军事演习开始了。首先出场的是一队神枪手,他们当着客人的面表演速射,在美制冲锋枪卡宾枪震耳欲聋的射击声中,干硬的泥土溅起朵朵烟花,两百米外那些竹靶子纷纷稻草人般四分五裂。接下来是轻重机枪把一千多米外山头上的小树像割草一样轻易击成几段。最后登场的是新式无后坐力炮,黑色的粗大炮筒令客人们大开眼界,他们看见炮手把牛腿粗的炮弹填进炮膛时都惊呆了。果然,大炮一响,许多客人变成聋子,头嗡嗡直响。硝烟散去,他们赫然看见,对面山坡上一座石头房子已经荡然无存。
事实胜于雄辩。土司脑袋好像被洗过一样亮堂,先前那些抵触的思想和念头全都被扔进萨尔温江去了。他们心服口服地相信,服从李主席和汉人军队不仅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是非常必要的。
后来有个军官出个节目叫“赌人头”。赌博在尚武的金三角掸邦部落很盛行,什么都可以赌,什么矛盾纠纷都可以通过赌博来解决,比如寨子与寨子,部落与部落发生纠纷,双方土司就把老百姓集合起来解决,解决的方法之一就是赌博。可以掷骰子,看鸡骨,比枪法,油锅里面捞瓦片决出胜负,没有道理可讲。土司都豢养着许多枪手亡命徒,有时赌注下得很大,赌牛羊田地女人,如果双方土司较上劲,他们会因此赌上银元鸦片和官寨。但是这次赌博不同,赌注下的是人头。方法是枪手将一只盛满米酒的酒碗击碎,但是酒碗不能放在地上,而是被人顶在头上。
关键在于,顶这只碗的不能是随便什么人,必须是土司本人。
李国辉站出来,他是大名鼎鼎的汉人“召龙”(大官),将一只粗瓷碗顶在头上,枪手站在二十米开外,枪一响,酒碗早已碎了。李国辉脸不改色,换了碗再射。酒席上的土司个个目瞪口呆,酒吓醒了,他们哪里有胆量上场赌命?即使杀人不眨眼的暴君如法国路易十六,杀的都是别人,轮到自己被杀也会尿裤子。大凡与优越生活特权相伴的人决没有不怕死的,他们爱惜自己胜过爱惜别人,所以这些世袭土司一旦要站出去给别人当靶子,竟没有人敢站出来逞英雄。谁都知道,那个打枪的人只要心跳快上那么一点,手抖那么一点,土司老爷的好日子就算过到头了。
鸿门宴结束,晚上节目是放电影。
这些好莱坞产品都是由美国飞机从天上空投下来的,结果可想而知,银幕上下雨,土司就赶快叫人打雨伞,火车隆隆地开过来,便有人惊叫着逃出场外去。总之这个世界乱了套,直到电影结束,土司还是不能明白,为什么天空、大地、水、树木、风,还有那么多人、房子都被装在一只铁匣子里面?惟一的解释就是,汉人军队得到了神的力量。
作为精神和物质的被征服者,第二天所有的土司都乖乖地在一份拥护汉人军队的宣言上按上了手印。作为答谢,李弥赠送土司们一批美国军需物品:罐头、香烟、手电筒、打火机、高级布匹(降落伞)、防水帆布,还有少量枪支,并许诺将永久保护他们在金三角的利益。
5
十多天后一个惊人的消息传开来:孟畔土司出门时被土匪杀死,官寨也遭到洗劫。钱运周奉命出动,抓住一伙土匪,统统就地枪毙,平息匪患。于是刀土司名正言顺地接管了孟畔领地,一跃成为金三角势力最大的土司。
自从在孟萨吸毒之后,钱大宇在我心目中变得越发神秘莫测。他究竟是什么人?从事什么职业?有什么背景?是贩毒集团,还是台湾派来的特务,或者是什么秘密组织成员?他为什么关心我的采访,仅仅因为同他父亲钱运周有关?
我想,我在对方心目中是怎么回事呢?作家,采访?还是另有企图?我想他大约也觉得邓贤是个身份神秘的家伙,因为我们都没法窥破对方的秘密。离开孟萨前,我提出上拉牛山口看看,听说那里还有部分战场遗迹,而李弥时代最大规模的战争就发生在那里。
我们的汽车开出一段砂石路面,很快就上了山。最初路面尚可,汽车开得较快,道路两旁的掸族山寨一晃而过。这条公路是通往山外的惟一公路,但是很少看见对面有车过来,冷清清的路面让人感到寂寞,偶尔见掸族人赶着牛车慢吞吞地走路。随着山势越来越陡险,路面变得越发糟糕,经雨季浸泡而变得又滑又软的红泥好像牛皮糖一样包裹着车轮,汽车不仅在坑坑洼洼的路面上跳舞,而且像个脚步不稳的老人趔趔趄趄直打滑,我的心提到喉咙眼上了。
忽然间就出事了。
我还来不及反应过来,汽车轰的一震,我们的头一齐重重撞向车顶,原来汽车滑进路边水沟里。幸好是公路内侧,我们爬出车来向外面看看,个个都变了脸色。公路外侧是座云遮雾绕的深谷,能听见溪水在谷底吼叫,上帝保佑,要是他老人家让汽车滑向另一个方向,我们只好永远从这个险恶的世界上消失了。
好容易把车弄出水沟,司机小董说什么也不肯往前开,车是他一家人的谋生的饭碗,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这个蚀本生意就做大了。我认为安全第一,但是效率也很重要,如果司机有把握开下去,乘车总比走路好。钱大宇的态度很奇怪,他既反对开车,也反对走路,他说:“要是走路,今天夜里也走不到,要是开车,下次一定往外面打滑,不然我们来打个赌。”
我说:“你要怎么样?调架直升飞机来?”
他望望山头,很有把握地说:“前面有个寨子,司机你把车开下山等着,我们骑马上山。”
汽车留在公路上,我只好跟着他,步行大约二三十分钟,就看见芭蕉树丛中露出几幢铁皮屋顶。在金三角,人们盖房子一律采用铁皮顶,既不用砖瓦,也不用茅草,你看见哪里有铁皮顶在太阳下反光,哪里就有人家和山寨。面前是座汉人寨,说得好听是华侨,其实就是当地山民,在我看来同掸族山民也没有什么区别。他们说的都是掸族话,钱大宇同他们叽叽咕咕说一阵,我一点也听不懂。一个男人同意为我们当向导,说好我付路费,两百泰铢,约合人民币五十元,我认为这个价钱不错,他牵来两匹矮种马,跟中国内地毛驴差不多,我们一人骑一匹就上路了。
这是我有生以来头次取得骑马的经验。矮种马的胯骨一动一动,肚子也一鼓一缩地呼吸,仿佛提醒我胯下是个活物。我感到很别扭,这个活物无论上坡下坡,随时让我神经紧张,我觉得自己这么沉重的身体压在这头可怜的牲口身上,而且坐不稳当,老是滑来滑去,弄出一头汗来,好像跟谁搏斗一样。我相信自己的表情看上去一定可笑极了。山民姓秦,皮肤黢黑,属于那种不好辨认年纪的人,我认为他的年龄应该在二十岁到五十岁之间。他看出我很紧张,就用汉话安慰我说:“不要紧,这匹马能驮二百斤呢。”我说:“是吗?驮这么重,一天能走多少里?”老秦说:“八九十里地吧。”我听出老秦有云南口音,就问他是哪儿人?他茫然地摇摇头,好像没有听懂。我说:“我知道你是汉人,老家在云南什么地方?”钱大宇在后面接口回答:“他们在金三角几代人,哪里弄得清云南老家在什么地方?”
山上雾大起来,如果从山下看,这不是雾,是云,山道上到处湿漉漉的。马儿驮着沉重的我倒没有什么抱怨,它很听话,任劳任怨,头有规律地一点一点,好像在背诵英语单词。我渐渐习惯同它和谐相处,不再紧张。树林越来越高大茂密,空气中有种浓浓的腐叶生霉和动物的腥骚气味,四处寂静无声,只有树叶上不时滚落很响的水滴声,好像下雨一样。这是一处真正的热带雨林,我看见连空气也是绿油油的,玲珑剔透,我深深吸了一口气,浑身舒畅,有种醉氧感觉。我想森林多好啊,也许会有老虎、猴子,还有野象,但是最好不要有人。在这个世界上,人是罪恶之源,只要有人就会有污染,有犯罪,人类像丑陋的苍蝇,把文明的罪恶播向四面八方。
正想着,好像上帝有意验证我的预感,密林深处忽然冒出一队驮载货物的沉甸甸的马帮,与我们迎面相遇。空气中立刻多了一种浑浊刺鼻的人与动物的混合气味。我看见马背上耸立着结实的驮架,驮架吱吱呀呀响着,上面盖着油布,马蹄沉重地将泥水踏得飞溅起来。马儿喷着粗粗的热气,不时打着响鼻,看得出走了很长的山路。赶马人个个面色黢黑,戴尖竹笠披棕蓑衣,沉默地从我们身边擦肩而过。他们仿佛一心一意赶路,对狭路相逢的我们不感兴趣。我们赶紧让在一边,闻着空气中人马散发的浓烈汗臭,等待他们先过,这是山里的规矩,相当于交通规则的空车让重车。忽然有件什么硬邦邦的东西撞我一下,我被电击一般,险些叫出声来。原来这个赶马人的蓑衣下面,露出一截黑黝黝的枪管来。
天!走私毒品……匪帮!
2
我要说明的是,我决不是个勇敢的人,在我偶然发现这支武装马帮之后,我的心跳立刻发生紊乱,大脑缺氧,浑身发冷一样打哆嗦。我想我当时血压一定高得惊人。与贩毒集团迎面相遇,就跟与老虎迎面相遇一样,你能事先作出什么正确反应呢?我脑子一片空白,就像发生故障的电视屏幕。好容易等到这队人马走过去,什么事情也没有出,那些带枪的人对我们视而不见,我松了一口气,胆子立刻大起来。我掏出照相机,躲在树后想偷拍几张照片,这将是珍贵的现场抓拍,没准还能得大奖。这个想法令我激动得发抖。
突然一只大手从后面把我按倒在地上。
原来是钱大宇。他怒不可遏,恶狠狠地咬着我的耳朵嚷道:“你他妈的不要命了?你活够了,我可没打算跟你一起送命!”
等我从地上爬起来,马帮已经不见影子,相机镜头沾满泥水。我气得发抖,嘴唇哆嗦说不出话来,要不是这家伙横加阻拦,我相信照片已经偷拍成功,要知道我是多么需要照片,需要成功,将来我的书出版,这些宝贵照片表明我是冒着多大危险闯进金三角,拍摄下来关于丛林中贩毒集团的真实镜头。现在一切都毁了,毁在一个对写作和文学一窍不通的混蛋手中。
钱大宇看看相机,再看看愤怒的我,他没有说话,拾起相机扔给我,转身上马继续往山上行进。我无可奈何,只好怏怏地跟在后面。说实在话,此刻我无法怨恨或者跟他赌气,离开他我能上哪里去呢?
走了一程,钱大宇说话了。他说:“老兄,相机弄脏了,我很抱歉,回去我替你擦一擦。”
我懒得开腔,不想答理他。他知道我还在生气,就说:“你不懂金三角规矩,看见别人的事,把眼睛和嘴巴一齐闭上。不然你就大祸临头了。”
我问:“他们是什么人?毒品走私集团?”
钱大宇说:“也许只是一般走私,也许挟带毒品,谁说得清呢?”
我叫起来:“他们有枪啊!”
钱大宇回答:“这有什么稀奇?你问问老秦,他们寨子里谁没有枪?”
原来如此!我们又走了很久的路,终于在中午时分登上拉牛山口,这时老天好像欢迎我们到来,云开雾散,天空突然放晴了。我看见这真是一架气势雄伟的大山,山垭口像一扇小门,扼住孟萨坝子出口。极目远眺,蜿蜒的萨尔温江像一条跳跃的金腰带,环绕群山之间,在正午的阳光下闪闪发光。钱大宇指着脚下山头介绍说:“决战就在这里展开,我父亲受了伤,印度雇佣军司令自杀,李弥下令树碑纪念呢。”
向导老秦熟悉地形,带领我们拨开荒草,来到一座石壁下。我赫然看见一块石碑,高约两三米,阔一米许,其实也不是石碑,而是刻在石头上的一排文字。年代久远,石头慢慢风化剥落,那些字迹有的看得清,有的已不可辨认,我认出并抄录内容如下:
中国救国军亡永垂总指挥李弥中华民十一年亲立
我想起八十年代在滇西松山战场上也有一块同样的石碑,为李弥亲立,也是纪念同一支队伍阵亡将士忠魂,不同的那是抗日战场,军人为祖国而战,为驱逐侵略者而献身,而这里是缅甸,是金三角,他们算什么呢?侵略者?烈士?毒贩?非法武装?他们应该名垂青史,还是遗臭万年?
老秦动作麻利地拔去四周荒草,恭恭敬敬跪下来磕了三个头。他的神情极为虔诚,口中念念有词,是当地话,我听不懂。我悄悄问钱大宇:“他是残军后代?”
钱大宇语气淡淡地说:“他爷爷和大伯都死在战场上。”
我觉得一股寒气从脚下渗出来。我说:“拉牛山决战你们死了多少人?”
这个“你们”很生硬,不像同胞,很没有同情心。钱大宇看我一眼答:“好像有五六千吧,但是消灭敌人一万多。”
我自豪不起来,这个数字令我震惊,相当于集体屠杀!我想象不出,数以万计的军人尸体铺满山野是怎样一种壮烈场面!但是五十年岁月过去,战争硝烟散尽,弹指一挥间,拉牛山依然山明水秀,郁郁苍苍,但是那些生命却化作泥土,化作轻烟,消失得无影无踪。
…………
下山已是夕阳西斜,我看见一头真正的野兽,那是一头美丽的褐色山鹿,披着金灿灿的晚霞从容不迫走过山坡,走过绿油油的大自然,然后从我们视线中消失。我呆呆地看着这个自由的美丽生命走远,心中一时充满感叹和惆怅。如果金三角没有枪声,没有毒品,它本该是万物的乐园啊!
这天的惟一的遗憾是相机进了水,没能拍成照片。
3
我继续关注国民党帝国在金三角的崛起。
封疆大吏李弥踌躇满志,该做的姿态都做了,反攻云南也反攻了,朝思暮想的美国武器搞到手,应该说最大赢家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更不是美国人,而是他李弥。一切皆在运筹帷幄之中。搞政治就是这么回事,反攻是态度,打仗是实力,谁能阻止他打败仗呢?就像谁也无法制止天要下雨一样。他正是因为“反攻失利”而博得头彩,中了一个大奖。台湾卵子大的地方,达官显贵多如牛毛,而在这片面积比台湾大几倍的金三角,他李长官的头昂得比谁都高,谁敢与他比肩?他是金三角的主宰,金三角的太阳,一切惟他意志是从。权力,多好啊,就像日月和风一样无所不在,有权力就有一切。
军权是权中之权。李弥回孟萨第一件事就是进行军队大整编。整编后的反共救国军摇身一变,俨然具备小国防部的格局:一个总部,下辖司政后三部,一个北方作战指挥部,四大军区,三大主力师,十八支挺进纵队和四个边区独立支队。他亲自任命高级军官,其中包括副总指挥多名,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军区司令以及军、师长均为他从香港带来的亲信。原复兴部队只除一个李国辉继续留任师长外,其余皆名落孙山。而担任第一副总指挥的不是别人,正是刚刚偕同李太太从昆明狼狈出逃的前第八军副军长柳元麟。
空运来的武器被严密存放在孟萨大本营中,这批武器足够装备三个国际标准师,但是李弥并不打算把它们全部补充到部队去。他只将其中部分配备主力师,其余各纵队支队杂牌军游击队,武器装备自行筹措。他的做法与从前蒋介石如出一辙:亲疏有致,内外有别,中央军是嫡系,地方部队杂牌军是野种,听任自生自灭。
从前李国辉时代,复兴部队对掸邦土司采取安抚政策,经常送礼物武器笼络他们。但是李弥不同。李弥是堂堂国民党陆军中将,反共救国军总指挥兼云南省主席,如果按清朝官位,少说也得封个从一品文武大员。那些土司算什么呢?充其量是些不开化的蛮子、部落酋长,他们有什么资格与李长官平起平坐,被他待若上宾呢?如果说从前李国辉力量薄弱有求于土司,“借土养命”,那么以现在反共救国军的强大实力,谁还敢与他公开作对,在老虎头上捋毛呢?
五十年代岁末的一天,李弥派出信使向金三角各大土司送去请帖,通知土司三天之内到孟萨开会,请帖对会议内容含糊其辞地称:“协调有关方面……管辖职能范围以及鸦片粮食税收等重大问题,恭请出席为要。”云云。
钱大宇的外公孟萨土司刀栋西是最早接到开会通知的人。
世袭大土司对汉人这种集中议事方式感到很不理解,因为在金三角,土司老爷从来不开会,如果有什么要事相商,大家就像走亲戚一样,你来我往,马队浩浩荡荡,今天你到我官寨来,明天我到你府上去,所以大家从来没有聚在一起的机会。据说从前土司父亲的父亲也就是老土司曾经接到一次类似的开会通知,那次是仰光英国总督专程派信使送来的,结果老土司的马队在路上走了三个月,到仰光后却只开了一天会。
开会内容同样让刀土司感到迷惑不解。“重新协调……管辖职能范围”是什么意思?土司的领地是从老土司手中传下来的,老土司是从更老的土司手中传下来的,就像坝子里的水是从山里流下来,大树再高也得从树根开始生长一样,难道那些汉人不明白,水是不能流回山上去的,树是不能从树梢开始生长的么?还有“鸦片、粮食、税收”是什么意思,莫非那些从中国来的汉人要土司向他们交纳鸦片、粮食和税收不成?
不仅刀土司不明白,连足智多谋的汉人管家也弄不明白,这是一个从来没有人遇到过的难题,连官寨里胡子最白的老人也没有遇到过,所以人们都被难住了。土司只好悄悄派人把当军官的汉人女婿钱运周叫回官寨,好把事情弄个明白。
钱运周也不清楚会议内情,但是他能猜到李长官要统一金三角的决心,没有人能够阻挡李长官的意志。所以他委婉开导土司岳父“识时务者为俊杰”的道理,指出开会无论李主席号召什么他都要无条件服从,带头拥护响应。
尽管这个道理属于汉人而不是掸族,刀土司对这种“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的汉人逻辑很抵触,但是他懂得要服从强权意志这个大原则,这个原则在地球上是一致的,好比动物天生知道弱肉强食的道理,所以土司老爷勉强接受了女婿的建议。后来他果然处处按照女婿的指点去做,获得意想不到的好处。
4
我能想象这是一个充满杀机和危机的会议,当身着国民党将官制服的李主席满脸微笑,亲自同与会土司握手,土司个个矮了半截,唯唯诺诺。副官长宣读以李主席名义发布的三项政策:第一,所有金三角地区,北至佤邦果敢,南到孟卯耶县,均为反共救国军管辖区。第二,凡军管区内居民,均要征收赋税和公粮,征收数目由军方决定。土司、山官和头人享有免交特权。第三,对鸦片实行统购政策,由军方统一制订收购价,任何人不得私自买卖鸦片。商人须经批准方可进入军管区做生意。最后这位汉人军官杀气腾腾地补充道:“凡遵守政策条令者,其领地将受到军队保护,违者严惩不贷。”
众土司面面相觑,敢怒不敢言。
几百年来,萨尔温江以东这片辽阔的崇山峻岭都是土司老爷们的领地,山高皇帝远,连仰光的英国人都管不到这里来,一切由土司说了算。金三角是土司的家,土司是金三角的老爷。奴才向老爷交税纳贡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商人当然也要纳贡,那是向土司纳贡,纳什么贡和纳多少贡视土司心情兴致而定。可是眼下这位在中国云南打了败仗的汉人主席却要像主人一样命令商人和老百姓向他交税纳贡,还要抢走土司世世代代赖以为生的鸦片生意。你是汉人主席,要收税回你们云南收好了,怎么收到金三角来了呢?
土司们脸色都很难看,会议陷入僵局。问题是他们没有胆量反抗,因为他们的眼睛决不会看不到在会场外面游动的武装士兵,还有那些虎视眈眈的机枪大炮。这就是强权政治。李弥是政治家,他当然知道怎样对付这群没有见过世面的土司老爷,他没有强迫大家表态,而是摆下丰盛的酒席请土司们喝酒。
李主席亲自向土司敬酒,这杯酒当然是苦酒,喝得比较勉强,但是没有人敢不喝下去。钱大宇的外公刀土司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下子完成认识过程的飞跃。当尊贵的汉人主席同他干杯时,尽管他心里并不高兴,也有许多抵触和思想疙瘩,但是他牢记女婿的话,坚决服从汉人长官领导。掸邦有句谚语:猴子不该与老虎争食。如果老虎不幸闯进猴子家里,那并不是老虎的错,猴子只好自认倒霉。作为猴子之一的刀土司果然旗帜鲜明地宣布站在汉人一边。
“我,刀土司……欢迎李主席住在孟萨,这是我刀土司的光荣。”可怜的土司老爷一看到汉人主席亲切和鼓励的目光,立刻乱了方寸,话也说得词不达意:“今后,我们掸邦人,把粮食统统交给李主席,买卖也做在一起,饭也吃在一起,就像亲兄弟一样……你们都知道,我的女婿,也是李主席的军官,我们都是亲戚。”
这番逻辑思维混乱的表态至少传达出一个令人满意的思想,那就是坚决拥护汉人军队的领导。这当然有些像带头在条约上签字的卖国贼,出卖的不仅是自己,还有其他土司的共同利益。许多人坐不住了,纷纷表态服从李主席,当李弥得知原来大土司的女婿就是师参谋长钱运周时,便大大地赞扬了孟萨土司,并号召所有土司向他学习。当然也有少数坚持不识时务的人,孟畔土司自恃与东枝掸邦首领有亲戚关系,带领另外一群小土司和头人提前退出会场。李弥脸上也不见生气,他对大家讲了一个驴子欺骗老虎的笑话,说的是驴子自作聪明,结果被老虎作了午餐。听得土司毛骨悚然。
当客人酒足饭饱醉眼朦胧的时候,一场事先安排的军事演习开始了。首先出场的是一队神枪手,他们当着客人的面表演速射,在美制冲锋枪卡宾枪震耳欲聋的射击声中,干硬的泥土溅起朵朵烟花,两百米外那些竹靶子纷纷稻草人般四分五裂。接下来是轻重机枪把一千多米外山头上的小树像割草一样轻易击成几段。最后登场的是新式无后坐力炮,黑色的粗大炮筒令客人们大开眼界,他们看见炮手把牛腿粗的炮弹填进炮膛时都惊呆了。果然,大炮一响,许多客人变成聋子,头嗡嗡直响。硝烟散去,他们赫然看见,对面山坡上一座石头房子已经荡然无存。
事实胜于雄辩。土司脑袋好像被洗过一样亮堂,先前那些抵触的思想和念头全都被扔进萨尔温江去了。他们心服口服地相信,服从李主席和汉人军队不仅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是非常必要的。
后来有个军官出个节目叫“赌人头”。赌博在尚武的金三角掸邦部落很盛行,什么都可以赌,什么矛盾纠纷都可以通过赌博来解决,比如寨子与寨子,部落与部落发生纠纷,双方土司就把老百姓集合起来解决,解决的方法之一就是赌博。可以掷骰子,看鸡骨,比枪法,油锅里面捞瓦片决出胜负,没有道理可讲。土司都豢养着许多枪手亡命徒,有时赌注下得很大,赌牛羊田地女人,如果双方土司较上劲,他们会因此赌上银元鸦片和官寨。但是这次赌博不同,赌注下的是人头。方法是枪手将一只盛满米酒的酒碗击碎,但是酒碗不能放在地上,而是被人顶在头上。
关键在于,顶这只碗的不能是随便什么人,必须是土司本人。
李国辉站出来,他是大名鼎鼎的汉人“召龙”(大官),将一只粗瓷碗顶在头上,枪手站在二十米开外,枪一响,酒碗早已碎了。李国辉脸不改色,换了碗再射。酒席上的土司个个目瞪口呆,酒吓醒了,他们哪里有胆量上场赌命?即使杀人不眨眼的暴君如法国路易十六,杀的都是别人,轮到自己被杀也会尿裤子。大凡与优越生活特权相伴的人决没有不怕死的,他们爱惜自己胜过爱惜别人,所以这些世袭土司一旦要站出去给别人当靶子,竟没有人敢站出来逞英雄。谁都知道,那个打枪的人只要心跳快上那么一点,手抖那么一点,土司老爷的好日子就算过到头了。
鸿门宴结束,晚上节目是放电影。
这些好莱坞产品都是由美国飞机从天上空投下来的,结果可想而知,银幕上下雨,土司就赶快叫人打雨伞,火车隆隆地开过来,便有人惊叫着逃出场外去。总之这个世界乱了套,直到电影结束,土司还是不能明白,为什么天空、大地、水、树木、风,还有那么多人、房子都被装在一只铁匣子里面?惟一的解释就是,汉人军队得到了神的力量。
作为精神和物质的被征服者,第二天所有的土司都乖乖地在一份拥护汉人军队的宣言上按上了手印。作为答谢,李弥赠送土司们一批美国军需物品:罐头、香烟、手电筒、打火机、高级布匹(降落伞)、防水帆布,还有少量枪支,并许诺将永久保护他们在金三角的利益。
5
十多天后一个惊人的消息传开来:孟畔土司出门时被土匪杀死,官寨也遭到洗劫。钱运周奉命出动,抓住一伙土匪,统统就地枪毙,平息匪患。于是刀土司名正言顺地接管了孟畔领地,一跃成为金三角势力最大的土司。